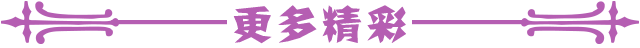编 者 按
自水墨写意的文人画风兴起并在中国画坛占据主导地位以来,色彩在中国画中日渐遭到排斥而处于缺失地位。但水墨写意的反色彩理论,所谓“运墨而五色具”,实质上并未改变其对哲学色彩论与五原色体系的理论隶属,不过是它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已,其大文化背景仍为阴阳五行学说。然而,色彩的缺失毕竟是一个遗憾,尤其是在与唐代及其前绘画的五彩缤纷的对照之下。尽管本世纪以来有不少中国画家致力于为现代中国画找回缺失的色彩并有所成就,但多彩化的趋势尚未形成。作者认为,中国画再度辉煌的希望在对哲学色彩论与五原色体系的重新发现、认真研究及创造性运用上。
一、色彩的缺失与复归
自北宋时代开始,文人画思潮渐渐在中国绘画中占有主导地位以来,水墨写意的画风以一种排斥色彩的态度,迅速在中国画的传统中营造出过于冷静的理性主义氛围,所谓“运墨而五色具”,就是说哪怕是在被古代人以两种色彩的名称——“丹青”来指代的绘画活动中,色彩也退居于只能依靠观者的想象力在幻觉中复原的地位。
当然,就艺术学的原则来讲,单色画的出现应当被视为一种文化在艺术上成熟的标志,但是,在公元十世纪以后的古代中国艺术中,以水墨画为代表的单色绘画成为所有画家追寻的最高级艺术形式,并因此而形成历几个时代而不衰的压倒优势,乃至在思想深处排斥一切色彩竟成了绘画最基始的语言之后,我们就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弊病,或者说是一个民族的怪癖了,尤其是如果比较一下这个时代来临之前的唐代艺术的话。我们常常说唐代绘画的雄强博大是后来中国绘画所难以企及的,究其原因,宋元以后绘画中色彩的全面丧失以及水墨画的迅速扩展在其中也许起到了非常大的反衬作用。
▼ 以下作品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狩猎出行图》(局部),章怀太子墓,唐代壁画
并不是说宋元以后的绘画中完全没有色彩,而是必须指出经过文人画思潮的洗礼之后,中国画家不由自主地从内心深处取一种与文人水墨写意认同的态度,从而轻视色彩,将色彩的运用视作可有可无的辅助手段,并因此导致了与唐代以前绘画比较起来在色彩的使用技巧上极大的倒退。唐代以前那种自由、活泼、强烈、真率的用色技巧消失了,剩下的是呆板、拘谨、毫无生气与陈陈相因。拆碎了七宝楼台,不成片段的一瓦一石成不了大的气候,尽管我们还勉强能举出赵孟頫、钱选、仇英、陈洪绶、恽寿平、华喦等等前后不相属连的几位画家对色彩略有偏好,但底气也不免愈来愈弱,绚丽丰富的光与彩渐渐湮没于日趋简单重复的水墨黑白之中。
近代以来,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传统文化结构的溃散必不可免,反映在绘画上,则表现为突破原有陈陈相因的绘画样式,将重视笔墨韵味超过重视物象造型的关系颠倒过来以及为中国绘画找回色彩等等。对于色彩问题的重新重视以清末民初海派画家的作品表现得最为突出,任伯年、吴昌硕为首的一批人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创获。尽管吴昌硕号称学画于任伯年,但在色彩的运用技巧上,两人之间却有极大的不同。任伯年绘画的用色正如不少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极有可能受到西洋水彩画的启发,在他的作品尤其是中年以后的写意花鸟画中,注重色阶的变化,利用色差关系,考虑环境色及画面的色调等等,确是中国传统绘画用色中极难见到的,就这一点说来,任伯年可算是中国画家中食洋能化的大师。如果说任伯年的做法丰富了中国绘画色彩技巧的话,那么,从他学画的吴昌硕却反而将这些技巧又简化到传统绘画的水平上。吴昌硕用色主要受到清末赵之谦诸人的启示,赵的色彩纯净而明亮,缺点是单薄而平板,与物象本身的丰富性较少联系,吴昌硕则在纯净的原色中混入多变的墨色,使水墨交融的效果显得比任伯年墨色分离的效果更为厚重和丰富。任伯年善于使用复色、中间色,依靠原色不同比例的调和和渗混来取得光彩陆离的丰富印象,吴昌硕则仅仅使用少数几种原色,依靠这几种原色与不同水分和不同墨色的混合和搭配,产生浑厚而艳丽的印象。显然,与任伯年繁复用色的丰富性相比,吴昌硕这种简单原色与墨色搭配产生的丰富性更加适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习惯,乃至有不少人将任伯年的绘画斥为“俗艳”而尊吴昌硕的风格为“古艳”,其间高下差别显示出的审美倾向,不言而喻。

任伯年与吴昌硕作品
值得重视的是,任伯年之后,他那种近乎水彩画的用色法即使在海派画家中也少有人能够继承,或者说,至少是继承者中没有青出于蓝的大师,而吴昌硕之后,直接受到他画法恩惠的大画家至少可以举出齐白石、潘天寿二人。齐白石将吴昌硕已经简化的用色法更加简化,他不像吴昌硕那样在原色中渗混墨色,而是直接用原色作画,但却始终将墨色作为一种基调,一种与原色的浓艳作成对比的因素来使用。与吴昌硕不同的是,他的墨外在于色,而吴则融浑于色,相同的一点则都是以传统的水墨黑白作为色调的基干,作为背景来展开,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来处理。为了与墨色形成对比而制造视觉上的张力,他们相同的另一点,便是在使用颜色的时候偏爱暖色,例如红(朱砂、洋红、胭脂)、橙红(朱磦、赭石)、黄(石黄、土黄、藤黄)等等,而较少使用石青、石绿等冷色,最常用的花青及由花青与藤黄混合而得的各种绿色,也只是作为墨色的辅助来使用。这一现象的文化背景应当被理解为传统文人水墨原则“运墨而五色具”在这个时代仍只是部分受到了挑战,暖色由于与墨色的差异太大而被分离出来,而不同深浅的墨色仍被画家视为包含了全部冷色的基本色彩,或者是在画面上除掉主要部分的所有次要色彩。吴、齐这种在水墨画面上加入简单色彩的做法产生了相当广远的影响,可以说整个现当代中国画大体上都没有摆脱他们开创的这种墨加彩的模式。对于文人水墨画传统说来,这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变革,但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如果再进一步,如果彻底抛弃水墨,那么,文人画的千年传统还能否继续存在?

《荔枝蚂蚱图》,齐白石
几乎与吴、齐水墨加彩的探索同时,张大千、于非闇等人也在为中国画找回色彩探索路径。张大千早年绘画深受海派画风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对于文人画传统中极其有限的色彩运用显得极不满足,同时又对绚丽的色彩有着某种天生的敏感,最后导致他将探求的目光移向唐代的壁画。由于唐代壁画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复杂色彩运用自如的娴熟技巧与后来文人水墨传统技巧的极大不同,张大千中年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文人画技法,转向几乎完全依靠色彩在不渗漏的底子上作画,这使他自己的艺术面貌显得十分与众不同。他对于唐代以前绘画色彩的发掘与模拟试验对现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应当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而且还将继续发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对古代最常用而后来几乎失传的矿物质颜料石青、石绿、朱砂等的复杂用法的重新发现,给现当代中国画色彩带来很大的改变。于非闇受张的启发将目光转向色彩的研究,他没有张那样直接到敦煌学习古代壁画的条件,而将注意力放在古代工艺品尤其是传世的宋元明时期的刻丝、刺绣等等上。“礼失而求诸野”,这些工艺品往往以前代大画家的作品尤其是色彩艳丽的作品为蓝本来制作,因此也间接保留了不少古代画家的色彩大样,于非闇由此也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然而,张大千内心深处仍蟠郁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文人情结,尽管他热情地为中国画找回色彩不惜远涉西域,但他仍然不能完全拒绝水墨的诱惑,尤其是在他晚年的作品中,仍不时弥漫起水墨的烟云。于非闇找到了古代画家常用的色彩关系,但在古代工艺品中也仅仅只剩下了这些关系,至于那些精妙的变化、复杂的技巧带来的复杂的色相都不可避免地隐没在历史的身后了。

《春色入帘》,张大千
除上述两大趋势代表了近代中国画对于色彩的追求之外,另有陈之佛及岭南诸家从日本画中汲取营养,虽然各有成就,对现当代中国画也有影响,但毕竟未成大气候,也与中国人的审美倾向稍有隔膜。
摆在当代中国画家面前的问题是,除了文人画的水墨传统,中国古代绘画究竟形成了何种色彩体系?与欧西绘画以光学和色彩学的进展为背景发展出来的科学色彩体系相比,中国风格的色彩体系有何特点?对于当代中国画艺术来说,这些特点有何意义?又如何在这些传统之上发展出当代中国画的色彩体系来,又不丧失传统深厚的人文价值?
在艺术上,所谓传统,很大程度上包含在具体的技巧和法则之中,而传统的变革,也往往是由具体的技法为起点并且最终又归结到具体的技法问题上,古今中外莫不皆然。中国画的色彩问题虽有极多的人关注,但从具体的用色方法、材料、工具上来突破者至今还未见到。如果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许将不会局限在这一问题之上,而是有关中国绘画在当今世界的命运这一重大课题了。
二、科学色彩论与哲学色彩论
随着现代科学的进展,由光学派生出来的色彩科学成为了西方绘画色彩学的基础,与古代、中世纪的绘画相比,近现代西方绘画的色彩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其特征是绘画色彩的应用已经具有相当明确的科学背景与理性内涵。而近现代中国绘画的色彩与传统中国画色彩相比却无论从基本原则、具体应用直到原材料及其制作方法,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同时,其特征在理论上也不十分明朗。但是,如果我们以近现代西方绘画的色彩理论与应用原则作为一种尺度,来检视中国绘画色彩的应用原则的话,中国绘画色彩的理论特征就明确地凸现出来了。
西方的色彩学认为,光是发生的原因,色彩只是人类对其感觉的结果。这是根据现代物理学、光学、生理学、心理学的一系列实验结果得出的科学结论。因此,对于自然光的光谱分析,奠定了色彩学上三原色理论的基础,而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光谱学的色彩序列很快地对绘画用色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与西方绘画的科学色彩学相对照,传统的中国色彩理论可以称之为哲学的色彩学。在人类已经有过的各种文明之中,没有哪一种文明或文化像古代中国文明那样重视色彩的象征意义、精神内涵与哲学价值,也没有哪一种文明将色彩作为哲学意义上的宇宙秩序来使用。根据阴阳五行原则,古代中国的哲人将色彩归类为五种基本原素,即青、赤、黄、白、黑五色,以这五种色彩分别象征自然界和社会人类的各个方面并组织成某种密不可分的关联结构。譬如,在空间方位上,五色分别代表东、南、中、西、北;在社会道德上,代表仁、礼、信、义、智;在个人情感上,代表喜、乐、欲、怒、哀;在四时节序上,代表春、夏、四季总和、秋、冬;在医学上,代表肝、心、脾、肺、肾五脏;在音乐上,代表角、徵、宫、商、羽五音以及五气、五味、五卦、五星、五神等等。古代中国人关于色彩的哲学判断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一些基本思想演绎开来,使中华文化从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直到生活起居和艺术创作都深受这种哲学色彩论的浸染。其实,建立在物理学光学实验基础上的现代光谱学色彩理论,永远无法完全满足人类对于色彩存在的全部情感需要,永远无法完全解答人类生活中出现的色彩问题,因此,色彩的本质既可以由科学的角度来观察,由科学的立场来解释,也可以由人生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和解释,中国式的哲学的色彩学非但不会因为其缺少实验科学的基础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或许在艺术创造上,反而会因为它重视人的主观情感和人的文化态度而更能与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相整合。

与西方的科学色彩论相适应,由现代化学工业生产出来的颜料可以满足光谱学色彩体系的全部要求,而中国的哲学色彩学理论下的颜料体系最突出的特征是其自然主义倾向。在中国画的颜料学中,基本的原则是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取能够显色的物质作颜料,并且不改变其原始的色相而直接施用于绘画。根据传统的分类方法,中国画颜料被分为石色(矿物质粉末)和草色(植物色素萃取物)两大类,都是采用天然原料直接加工制成颜色,仅有的例外是利用化学反应获得的银朱和铅粉,但由于其耐光性差和化学性能不稳定,极易变色,为许多画家所不取。如所周知,石色之中,红色系的颜料有:朱砂(属于辉闪矿类的一种天然物质,主要成份是硫化汞);朱磦(更细的朱砂粉末,色彩偏黄,为橙红色);赭石(是产于赤铁矿中的一种结核状物质,因其所含铁质的多少不同而有红赭石、黄赭石之分,各地所产原料色相也有明显的不同)。此外,还有银朱和黄丹,因用化学方法取得而呈色不稳,后来渐少使用。
黄色系的颜料有:石黄、土黄、雌黄、雄黄。这四种颜色除了土黄是天然黄色粘土以外,其余三种都是化学成分为三硫化砷的物质,出产在一起,因所含物质的比例不同而有色相的差别。
蓝色系的颜料有:空青、扁青、曾青、白青、沙青。以上各种总称石青,在现代化学上被认为是盐基性碳酸铜,因产地和原始结晶状的不同而有上述各种名称。由于矿物本身的纯粹程度和研磨的粉末粗细不同,显现出深浅不同的色相,通常又分为头青、二青、三青、四青来使用,颗粒愈细,呈色愈浅。
绿色系的颜料有:石绿、沙绿、铜绿、孔雀石。都是产生于铜矿中的结晶体,也因为粉末颗粒的粗细不同而呈现深浅不同的色相,通常也与石青一样,分为头绿、二绿、三绿、四绿,研磨愈细,呈色愈浅淡。
白色有白垩,是一种成分为炭酸钙的白土,使用的时间极早。后来又用海中的贝壳烧锻成石灰质,研成粉末来代替白垩。此外有用化学方法生产的铅粉,由于化学性能不稳定而极易变色,只作为一种低档的白颜料来使用。
黑色有黑石脂,即石墨,研粉加胶后,可作黑颜料使用。
以上六大系统颜色之中,青、绿两系通常被联系在一起,作为色相较近的一类来处理,这样,这五大类矿物质颜料正好满足了传统的哲学色彩论的“青赤黄白黑”五大类别哲学结构的需要。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先民们在生活实践中发现和总结了自然界中呈色物质并在实际应用中升华了对于色彩的情感需要,将其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与五行思想融会为一个文化网络,将天地自然宇宙万物都有序地组织进这个网络之中,从而赋予了色彩以精神的意义。对于色彩的哲学判断实际上是对于自然万物的价值判断以及万物之间存在关系的价值判断,因此,在最初的色彩使用上,往往与先民的宗教活动有关。在中国考古中发现的早期使用色彩的场合往往有宗教活动的背景,譬如山顶洞人在墓葬中使用朱砂,彩陶图案的红白黑三色组合,早期岩画的朱红图案等等,以至后来的墓葬壁画、宗庙壁画、宗教壁画中的大量浓郁色彩的使用,其在精神境界上对于观者人性的提升和人格的塑造能力,都无不源自早期哲学色彩论从阴阳五行思想体系中获得的精神内涵。
三、五原色体系的细节与变化
草色作为辅助色后来大量被应用到绘画创作之中,尽管这一类颜色更加丰富多彩,但仍只是作为五色体系的某种补充,而并没有在理论上产生新的哲学判断。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色彩学原则上容忍任何补充色和辅助色,因此,尽管草色的种类更多,来源更复杂,同时,呈现的色相如果用科学色彩学的眼光来看也更加不成系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但是,由于通过使用石色建立起来的五色系统牢固的哲学体系已然确立而不可移易,偶然性极大的多种不同色相的草色可以被轻易地组织到原有的网络之中,所以,草色的变化只是丰富了五色体系的细节,使其更加容易地应付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色彩需要。
草色系统的颜料都是自然界中植物色素的萃取物,将它们取作颜料,常常会受到时代、地域、民族和制取技术的局限,因而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以至于流传至今的古代绘画作品中,有不少颜色我们至今仍然搞不清楚它们的具体来源。但有一点是很确切的,那就是草色的使用晚于石色的使用。草色的制取技术也比石色的制取技术复杂,这也决定了其广泛应用于绘画一定比石色为晚。
汉唐时代的壁画大多使用浓重的石色,其间以少量草色作为辅助,魏晋以前,草色石色单独分开使用,魏晋以后,草色石色调合或套染的方法渐渐流行,到隋唐时代,壁画用色的技巧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水准,草色石色复杂的混合使用令唐代壁画呈现出光辉灿烂的效果,表现出爽朗、健壮、自信与富丽的时代精神。

《鹿王本生故事》,莫高窟第257窟,北魏
唐代以后,壁画渐趋衰落,卷轴画逐渐兴起,画幅的底子既已由粗糙宽广的墙壁转变为细致窄小的纸绢,那种大面积使用浓重鲜艳的石色的粗犷豪放的画法很快就让位给以“色薄气厚”为原则的层层渲染、石色草色调合使用的新画法了。这种在北宋画院中发展成熟的用色技巧与当时院体绘画的写实主义作风相始终。正当它以准确、细腻、精致的姿态达到完全成熟的状况时,以北宋文人为中心的水墨写意画风已经开始在画坛上弥漫开来。自此以后,中国绘画对于色彩的关注逐渐淡漠,从画家到普通民众的心理,也逐渐趋于认同黑白水墨画的艺术效果。

《供养菩萨》,莫高窟第401窟,初唐
但是,从中国绘画的色彩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画家在使用色彩或者排斥色彩的时候从来不拘泥于他们眼中所见的物象,从来不光是用色彩来表现自然物象的外在面貌。如前所述,中国的绘画色彩有某种很强的内在自律原理在支配着它的使用原则,那就是中国的哲学色彩论。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当主观的色彩学理论,也可以说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色彩学理论,尤其是当这种理论被纳入到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之中从而获得深重的文化背景之后,中国的哲学色彩论就成为了代表东方文化精神的色彩体系了。大约是在汉代时补入《周礼·冬官》的《考工记》说:“画绘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彩备谓之绣。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五行相生相克的原则本来是古代中国哲学中解释宇宙万物流衍变化生生不息的理论模式,被认为是一种普适性的真理,既然如此,当色彩作为一种符号被代入这个模式从而获得其相生相克的原则,也就给绘画中色彩的使用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因此,第五世纪时谢赫提出的“随类赋彩”一说,很可能不是如后人那样勉强把“类”字解释成“物”字,把“随类赋彩”解释为“随物赋彩”,而是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则,根据五行分类的生克制化原理来使用色彩。这一点如果参考古人留下来的作品可以得到旁证,因为实际上,直到十世纪的北宋时代,在院体画家的写实主义作风鼓励之下,“随物赋彩”才开始成为可能,而在此之前哪怕是鼎盛时期的隋唐时代,绘画的色彩也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与客观物象有着相当距离的主观的色彩。这种看起来与自然物象关系不大、理想主义作风浓郁的色彩恐怕不是随意敷染而成,其理论的依据,可能要追溯到《考工记》所记以“文、章、黼、黻”标志的相生原则和以“相次”标志的相克原则中去。除了北宋院体画家在短暂的写实主义作风笼罩之下,少数人曾经做到“随物赋彩”这种真正的描摹自然物象外在色彩的写实手法之外,大多数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画家,实际上都是哲学色彩论的支持者和实行者。唐代以前,是这种理论的成熟时期,有大量的传世作品可以作为例证,唐代以后,则是这种理论的派生时期。
从宋代开始流行的水墨画,虽然被认为是反色彩的绘画,但实际上却是由哲学色彩论的片面发展带来的一个意外结果。墨色在中国从来就不被认为是单纯的黑色,黑色只是哲学色彩理论中的五色之一,而墨色是玄色,“玄”是变化的意思。《考工记》在讲到五方五色时,将代表中央(地)的黄色与天相对,说“天谓之玄”,则是在五色之外又加了一个“玄”色。“玄”色究竟是什么色,历来各说不一,其实玄色是变色,并不特指某一种色相。《考工记》“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这一简单解释天的玄色为变色的文字之下,有一条郑玄注文说:“天时变,谓画天随四时色者,天逐四时而化育,四时有四色,今画天之时,天无形体,当画四时之色以象天也。”可以说是对什么是玄色的最好解释。墨色是有变化无穷的深浅浓淡干湿燥润以及各种浸洇效果的特殊的色彩,因此被认为是玄色,从历来制墨名家的斋馆堂号及他们的名字多与玄字有关这一现象,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运墨而五色具”这一文人水墨画的基本理论,正是建立在哲学色彩论的五色体系派生出来的玄色即变色的这一古老命题之上的。

《江山秋色图》(局部),赵伯驹,南宋
唐代以后,以草色为原料的淡着色从以石色为原料的重着色的辅助地位发展出来,逐渐自成体系,特别是在从南宋到元代这段时期水墨写意画风充分成熟之后,因淡着色作为水墨写意的辅助手段重又得到利用而引人注目。淡着色与水墨画法一样,都是从古代的哲学色彩论的五色体系派生出来的,虽然并不能完整地体现五色体系的理论而偏执于一端,却仍是哲学色彩论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根据淡着色画法的通常习惯,它只使用极少数的几种色彩,即属于冷色系统的花青,属于热色系统的赭石、藤黄、胭脂。在水墨写意时代作为辅助手段的淡着色系统的颜色,比起唐代以前重着色时代作为辅助手段的淡着色系统的颜色,数量上要少得多。花青的蓝色以及由花青与藤黄调合得到的各种绿色,只是作为黑色的补充色使用,赭石色与淡墨色相互辅助,与深黑色形成阴阳对比,胭脂则只是偶尔使用的点缀手段。这时候,重着色时代的作品中常常可以见到的由草色与石色的混合使用造成的丰富的中间色已经完全见不到了。但是,这种淡着色系统在其最根本的原则上与五色体系的理论完全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从来不以追摹物象的外在色彩、自然色彩为其目的,而是秉承五色体系注重象征的原则,更关心作为其基本目的的心灵的体验与情感的抒发。

《明皇幸蜀图》,李昭道,唐
中国绘画的哲学色彩论在近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潮流的激烈冲击并且处于弱势的时局之中时,曾受到过无情的嘲笑和无知的攻击,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愈来愈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在艺术创作上,西方科学的色彩论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科学发现的规律可以解决人生的许多实际问题,但人却不是完全按照科学的规律来解释,出于对科学色彩论的这种不足的补充,近代西方绘画的不少大师都关注到东方色彩的成果,也就是关注到中国的哲学色彩论的成果,尽管他们有可能实际上并不完全理解这种理论的意义。梵高、高更、毕加索、克里姆特、米罗等人为了打破西方传统科学色彩论的束缚,都借鉴过中国(东方)哲学色彩论的实际使用成果,但作为东方哲学色彩论的祖国的中国人,我们至今却并没有以足够认真的态度去总结这一理论,用现代的观念去整理、解释这一理论。中国绘画要想在当今世界占有一席之地,通过改变自己的哲学色彩论体系而屈从于已经显出弊端的西方科学色彩论体系,已经被近代以来数十年间的实验证明完全没有希望,只有对中国传统的哲学色彩论重新认识,并且以现代的观念与立场加以改造与整理,形成现代中国画的哲学色彩论,才是唯一的出路。
四、五原色体系中的色彩三要素
中国绘画所使用的各种石色颜料,都是矿物质粉末。这些矿石粉末无论研磨得有多细,调胶以后作为颜料,其色相(Hue)都非常稳定, 并且有极强的覆盖能力。但由于矿物质粉末不管研磨到何种程度,与植物色素比较起来都显得粗,如果过分稀释,在画面上则表现不出色彩的纯粹来,因此,矿物质颜料在彩度(Chroma)上的变化相对较少。至于色彩三要素(Color Qualities)的最后一个明度(Value)在矿物质颜料使用上的表现,古代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一样,也靠加入黑白二色来使色彩明暗层次得到变化。
在汉代以前的壁画中,大多直接使用原色而没有明度的变化,那时候白色只是作为五色之一来使用。由于色彩明度的变化只能依靠颜料中黑白分量的增加或减少来实现,因此,古人对于色彩明度的了解和使用,也就可以从古代绘画遗迹中颜料里有否调入黑白二色来判断了。现存敦煌莫高窟的北朝壁画中,有许多人身的肉色已变成为灰黑色,那就是当时画家在银朱、黄丹等颜料中调入白粉获得肉色,时间一久,产生化学变化所致,并非当初就是用的灰黑色。又有在石青中调入白粉获得的天青色等。可知北朝时期中国画家对于色彩明度的变化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

《车马骑从仪仗出行图》,陕西靖边县杨桥畔镇杨桥畔二村渠树壕汉墓
隋唐时代的绘画遗迹中,色彩的丰富与灿烂令人吃惊,色彩明度的复杂变化,大量中间色的使用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宋代画家在色彩明度的变化上更为细腻,除在石色中调合白色以外,这时更发现了套染的方法,就是在有些需要非常明亮的色彩的场合,先用白粉染出白色的底色,待干后再用较淡的颜料多次套染,使其显出明亮的彩色来。由于套染的方法对于色彩彩度的控制更准确,宋代以后为大多数画家所使用。
文人画盛行以后,先是水墨画流行,到明清时代,不少文人画家又在水墨的基础上另加色彩,不过这时候文人画家所使用的色彩,已经大多是草色系统的颜料了。明清文人画家崇尚水墨,以传统的重着色法为匠人之技,排斥艳丽厚重的石色,白粉作为五原色之一,也在被排除的石色之列,因此不用白色来调配色彩的明度,而利用画纸纸底之白来完成色彩明度的变化,并结合色彩纯度的增减,构成了文人画色彩的独特创作原则。这一原则一直沿用到现代中国画家的创作活动中,但大多数现代中国画家对于这种源自上古时期哲学色彩论五色体系的做法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只是习惯性地使用师徒授受流传下来的做法而已。
当然,色彩的精彩之处并不在色彩本身,而在于画家使用了它之后,色彩与色彩产生关系之后,在观赏者心目中所引起的印象。文人画的艺术创造原则最重要的一点是追求简括,从用笔、造型到色彩都是如此,所以,实际上过于复杂的色彩和过于繁难的用色方法与文人画的简括原则没有内在的一致性。明清文人画所使用的主要颜料不外是花青、赭石、藤黄、胭脂等有限的几种,而就是这几种颜色,在这个时期的使用方法,与唐宋以前重视色彩时代的使用方法比较起来,已经简括到不可同日而语。文人画的用色几乎总是在先已用水墨画好并已干透的画面上,用水作为媒介,将已加胶的颜料简单地敷染上去,而其色彩明度的变化,则依靠在白色宣纸上已经渗洇晕散的墨色变化来调剂。这种方法,清初以前的文人画家尤喜使用。在文人画的理论中,色彩是一种次要的绘画因素,总是被作为水墨的辅助手段来对待,乃至于到了20世纪前半叶,吴昌硕、齐白石等人直接用原色画出物象会被认为是一种创举。尽管如此,经由历史的筛选而保留在晚期文人画中的几种主要色彩,仍然留住了古代五原色的内在气质。花青通常直接使用,赭石常常被当作黄色来与墨色和花青作对比色使用,藤黄一般不直接用,总是与花青调合成各种层次的绿色作为深浅不同墨色的辅助色,至于胭脂,只是用于点缀。可以这样说,在文人画中,从来就不追求随物赋彩,以上提到的几种常用色,与墨色的黑和纸色的白,在文人画中构成了实质上的五色系统,尽管大多数文人画家对此并不一定具有理性的认识。

《虞美人图扇页》,佚名,宋
文人画常用的这几种颜色的色相都极为明丽,用在一起,互为比对,给人美感的程度很高。这几种颜色。经过长期的实验,制作都极精美,纯度很高,用在画上,往往比生活中实际所见的颜色更为鲜艳美丽,同时,文人画并不追求随物赋彩,常常只是概念似地将这些鲜艳美丽的颜色直接点染到画上,因此,画上物象的颜色,自然比现实生活中物象的颜色更纯粹,更引人注目。这一点往往为接受了西方科学色彩论的人所诟病,也往往使对中国画理论没有深切了解的中国画家自惭。但我们知道,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人类对日常生活中很少见到的色彩产生的兴趣最大。同时,色彩中有积极性色与消极性色,前者引人兴奋,后者令人沉静,一般说来,纯度高的色彩都相当积极,容易刺激人使之兴奋不已,即便是冷色中的青、绿,只要纯到一定程度,也都往往会对人产生兴奋作用。文人画的用色技巧以及颜色本身,都能满足上述要求,这或许是千年以来中国文人画用色习惯沿习不衰的原因。
近代以来的中国画家较传统文人画家更多地注意到了色彩的作用。齐白石从吴昌硕的墨加彩模式中发展出墨与色分离的技巧,提高了他的作品中色彩的彩度,他的厚重的、饱和的、单纯的用色令人刮目相看。潘天寿则更多地注意色彩的明度,他在已经完成黑白框架的画面上预留出大片空白,然后施以大面积的淡彩。与齐白石不同,似乎潘天寿更理解文人画传统中的用色技巧,他恪守传统文人画常用的几种颜色而且往往更趋单纯,利用大片纸底的白色,施以浓度不是很高的单纯色,这样,由于白纸的映衬,他的色彩获得一种高明度的效果。

《雁荡山花图》,潘天寿
文人画的传统尽管在现代中国画中得到了一定的发扬,但中国绘画长期以来对于色彩的使用经验与审美趣味并不仅止于此,与唐代以前中国画绚丽光华的色彩比较起来,文人画色彩简直可以被称为不肖子孙。与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家们不同,当代中国画家的目光所及,要宽广得多,深远得多,思想上的束缚与戒条也要少得多,在清末以来中国画家对于色彩的重新探索基础之上,相信未来中国画在色彩方面,必将有一个灿烂光华的新境界。
五、现代中国绘画的多彩化趋势
色彩是绘画中流动的生命。当文人画逐渐兴盛,传统绘画中水墨黑白渐渐将色彩逐出画面时,中国绘画的生命之源也在逐渐枯竭。因此,近代中国社会从传统转入现代的大变化一经开始,与传统的皇权至上完全不同的现代平民化多元社会一旦出现,在绘画艺术上最重要的反映之一,就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画家为现代中国绘画找回色彩的不懈努力。这显示了在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现代社会中,在新的环境与新的刺激下,蛰伏在窘困的文化传统中的潜在生命力,已经开始重新涌动。
实际上,传统的价值,正在于它对于现代人的意义,一个囫囵的、不可分解、不可改变的传统对于现代人来说只是历史,只有当它溶入到现代生活之中时,才显示出意义来。历史学家所谓“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说的正是只有用现代人的立场来理解和使用历史,黑暗而死寂的历史才会光明而鲜活起来。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哲学色彩论及其在绘画上的五原色理论体系,如果不被现代中国画家所理解和使用乃至创造性地发展,其价值也是相对有限的,只有依靠现代中国画家创造力的激活,它才会发散出应有的光辉。

《石榴》,吴冠中
但正如西哲所言西方绘画的色彩与透视理论和西方的对位音乐、股票市场、远距离通讯甚至导弹技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样,中国古代哲学色彩论及其应用原则五原色体系经过中国历代画家数千年自觉与不自觉的使用,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中国绘画的创作、欣赏的原则与习惯,已经深深地浸染着这种理论,甚至或者可以说,正是由这些理论所滋养和培育出来的。我们常说绘画的中国风格、中国味、中国气派,其中的内在素质,正有这独特的哲学色彩论及其五原色体系在发生着精神底蕴的巨大作用。当然,作为一个现代画家,我们并不需要回到古代中国画家的制作水准和认识水平上去,但仍然有必要弄清楚自己身处的文化的脉络与精神,才不至于随波逐流,尤其是在现代中国这样一个日趋开放性的、多元化的社会中。
或许正是由于现代中国社会的日趋开放和多元化,我们深感哲学色彩论及其五原色体系在现代的应用,应当有一个相当大的改变弧度。正像在西方科学色彩论培育发展出来的现代西方绘画中渗入东方色彩一样,哲学色彩论的现代应用必须考虑西方现代色彩学的基本原则和最新进展,考虑西方色彩学的应用实践及具体技巧,同时又不放弃自己的立脚点和独特的视角。同时,对于古代用色技巧的发掘和复原、改革和发展也相当重要,譬如唐代壁画中的大面积厚涂色、宋人的层层套染以及三矾三染等等,都具有巨大的艺术表现能力与可以拓宽和变化的余地。
总之,从文人画的黑白世界或墨加彩的灰暗模式中走出来,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画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日本绘画曾经深受中国文人画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也将称作“南画”的中国文人水墨奉为正宗,但从明治维新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代化过程中,由于日本社会也由定于一尊的传统皇权社会转变为开放的、多元化的现代平民社会,大约自富岗铁斋以后,日本画家基本上再没有以水墨画著名的人,而自明治时代的横山大观、菱田春草诸人起,重视色彩的传统开始形成,到现在已经成了日本绘画的基本特色。当然,现代日本绘画对于线条的表现过分忽视是其弱点,但其在色彩上的变化,或许可以说明现代社会对于绘画的要求所在。

《屈原》,横山大观
与日本相比较,近百年来,中国趋向现代社会的过程过于曲折、复杂、痛苦和艰难,直到最近二十年,才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慢慢步入现代社会的正常运作之中。因此,从清代末年就已经出现的为中国现代绘画找回色彩的艺术思潮,在这个多难的时代里一步三回头、反反复复地蹒跚而行,直到现在,其多彩化的趋势仍然未能明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不再出现大的改变,中国绘画在现代社会中的多彩化趋势一定愈来愈强劲。与此同时,文人画中使用色彩时(包括现代中国画家的墨加彩画法)那种过分简捷随意的方法也将被更富于制作意味的技法所取代,实际上,现代中国画的多彩化趋势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更为丰富的色彩使用和制作技巧的发现来实现。

《王昭君図》,菱田春草
在中国哲学色彩论的鼓励之下,古代中国绘画中色彩使用的基本原则是并不过分考虑自然物象的色彩,而将其纳入到已经先行设定的色彩体系之中。这种方法,固然有其象征的意义与文化上的涵盖力,在传统社会几乎没有变化的文化氛围中,也满足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需要,但是,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原封不动地维持古代的哲学色彩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不过,目前最首要的问题是,现代中国画家大多对这种理论没有深切的了解,古代文献中关于这种理论的论述也极为分散而不成系统,传世的古代绘画作品作为哲学色彩论五原色体系的应用实践,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与研究。可以说,现代中国画家要恰当地利用这份遗产是相当困难的。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前提下,要保持自己的特色不被潮流所湮没就更为困难。正如现代中国画家中的敏感者所言,中国绘画要能继续存在而不被当今西方文化的侵蚀所吞没,唯一的出路,在于保持自己的特色,与西方绘画拉开距离。但保持特色也好,拉开距离也好,并不是保守主义地固守住并不十分可靠的传统,而是需要以中国文化精神为根基,开拓和丰富中国画的表现力,而现代中国绘画色彩表现能力的缺乏和低下,正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我希望,中国古代哲学色彩论及其五原色体系的重新发现与研究,能为现代中国绘画的多彩化趋势提供动力和精神支柱。
声明:本文摘自《文艺研究》(京)1998年03期
来源:诸子归来

注:本站部分文章及视频来源于网络,如侵犯到您的权利请联系我们,我们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