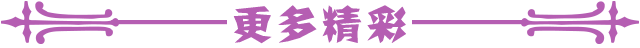导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了一本《丑的历史》,作者为翁贝托·艾柯(意大利),彭淮栋译。通本书讨论丑、残忍在艺术史中的表现和意义。下文是从中摘录的一小部分。我推这些,并不是鼓励师弟师妹们在毕业展大玩残忍,学校的规矩必须遵守,但我们必须思考这些“负面”的东西,才能让我们的思想有深度。
古人觉得某些音程不和谐会令人不快。有好几百年,音乐之丑最常见的例子是增四度,例如C—升F。中世纪认为这样的不谐和音十分乱人心神,因而将之界定为diabolus in musica(音乐里的魔鬼)。心理学家解释说,不和谐音有令人兴奋的力量。13世纪以来,音乐家也以这类音声制造特定效果。也就是说,这魔音经常被用来产生紧张、不安的效果,以及使人预感问题或情况即将出现某种变化,巴赫、莫扎特(《府乔万尼》)、李斯特、穆索尔斯基、西贝柳斯、普契尼(《托斯卡》)都用过,伯恩斯坦在《西区故事》里也用过。此外,增四度经常用来暗示地狱幽灵,例如柏辽兹的《浮士德的天谴》(Damnation of Faust)。
魔音提供我们一个极好的例子,用来为我们这本丑的历史作结,因为这题目可以激起一些反思。本书一路说来,有三项反思应该很明显:丑是相对的,随时代、文化而有别;昨天不能接受的事物,明天可能被接受;被视为丑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助于整体的美。第四项观察则引导我们匡正相对主义:如果魔音一向被用来制造紧张,那么,人类有些心理反应会历经不同时代和文化而维持不变。魔音逐渐被接受,并非因为它变得令人愉快,而正因为那丝地狱硫磺的气味从来不曾消火。
正因如此,魔音如今出现在很多重金属音乐里,吉米·汉克斯(Jimi Hendrix)的《紫雾》(Purple Haze)即为一例。有时候则挑明以“撒旦主义式”的挑衅形态出现,例如Slayer合唱团的专辑《音乐魔鬼》(Diabolus in Musica)。
电影《活死人之夜》(The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等恐怖片的导演乔治·罗梅罗(George Romero),曾就他的电影思想提出说明。他详述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金刚或哥斯拉动人的温柔,同时指出,他所拍的僵尸皮肤皱缩、腐烂,黑牙齿黑指甲,但他们是和你我一样有激情和需求的个体。他并且说:“在我的僵尸电影里,复活的死人代表一种革命,世界的一种根本变化,里面的人类角色无法了解,宁愿把这些活过来的死人视为敌人,其实他们就是我们。我以恐怖的方式使用血,使大众了解,我的电影是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纪实,而不是大量恐怖洒血的愚蠢冒险故事。”
这么说来,诉诸丑,是不是一种暴露邪恶存在的手段呢?罗梅罗自己承认恐怖片“票房冲天”。也就是说,他承认恐怖是因为有趣、令人兴奋而受到欣赏。恐怖变成歌颂邪恶也是如此,虽然只有一些边缘案例达到这种程度,例如心理变态的撒旦主义。
写到这里,我们面临很多矛盾。丑却可爱的怪物,像《E.T.外星人》或《星球大战》(Star Wars)里的外星人,不但令儿童着迷(他们还迷恋恐龙、神奇宝贝以及其他畸形生物),连成人也为之陶醉。他们还看脑浆四溅、血洒满墙的暴力电影,以此松弛身心,或读恐怖小说而乐在其中。
你不能一言论定大众媒体“堕落”,因为当代艺术也处理并赞美“丑”,只是不再以20世纪初叶的前卫艺术那种挑衅的方式。一些偶发艺术(happening)非但展示对一般人难有魅力的残缺肢体和其他身体障碍,艺术家还以自己的身体来承受血淋淋的折磨。
在这些例子里,艺术家说他们要藉此谴责我们这时代的种种残暴行为,但艺术爱好者到艺廊欣赏这些作品或表演却是带着愉快好玩的心情去的。

戈德伯为King Crimson合唱团的专辑In the Court of the Crimson King所作封面,1969
这些使用者并未丧失他们的传统美感,他们看见优美的风景、漂亮的小孩子或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平板电视,仍会产生审美的快感。
同样的这些人,今天接受家具设计团队、饭店建筑、观光业推销的古典悦目产品(看看拉斯维加斯那些威尼斯宫、古罗马餐厅、摩尔建筑),同时又光顾挂着20世纪前卫绘画(无论是真迹,还是复制品)的餐馆或饭店,而在他们祖父母眼里,这些绘画是违反古典观念的。
今天,我们到处听说,我们与各种对立的模式共存,美与丑的对立已不再有任何审美价值。丑和美两者都是可能的选项,我们以中性的态度加以体验。很多青少年的行为似乎印证了这个说法。电影、电视、杂志、广告和时装提供的美的典范和古代的并没有太大不同。我们也很容易想象一位文艺复兴画家会如何呈现布拉德·皮特、莎朗·斯通、乔治·克鲁尼或妮可·基德曼的脸孔。但认同这些观念(无论审美方面或性方面)的青少年也为一些摇滚歌手疯狂,而这些歌手的五官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看来必定是可恶的。这些青少年经常化妆、刺青、在身体各部位刺针穿洞,使自己看起来不是像玛丽莲·梦露,而是像玛丽莲·曼森(Marilyn Manson)。

妮可·基德曼,90年代好莱坞当红女星

玛丽莲·曼森,2005年3月


《扛十字架的基督》局部:迫害基督的人
耶罗尼米斯·博斯(荷兰)
根特艺术博物馆(荷兰)
在上面两幅对照插图里,你可以看到一个比较:一边是我们当代人穿鼻、刺耳、上下唇嵌入珠子,另一边是博斯画作里的两张脸,如出一辙。不过,博斯刻画的是迫害基督的人,在那个时代人的想象中是野蛮人或海盗(我们别忘了,一直到19世纪晚期,精神病学家还认为刺青是堕落的象征)。
今天,身体穿洞和刺青至多被视为一个时代的挑战姿态,大多数人的确没有视之为犯罪——一个舌头穿珠或小腹纹龙的女孩子可能参加和平示威或为非洲饥饿儿童游行请命。

庞克摇滚歌手,1998年5月
年轻人、老年人似乎都不认为这矛盾很严重。19世纪晚期的唯美主义者偏爱尸体般苍白的美,藉以挑战或拒斥多数人的品味,他知道他为自己培养波德莱尔说的“恶之花”。这类人选择恐怖,完全因为他们决定做一个位他们超乎“心态正确”的群众之上的抉择。
今天的年轻人炫耀纹身刺青或蓝色刺猬头,却是为了感觉像别人。他们的父母到电影院欣赏从前只有解剖室看得见的场面,也是因为大家都这样(cosi fan tutti)。
日常生活中,恐怖的景象包围我们。我们看见儿童饿死、只剩骨架、肚子肿胀的镜头;们看见一些国家的妇女被入侵的军队强暴,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众遭受酷刑,正如我们不断看到并不久远以前瘦得只剩骨架的人被打入毒气室送命的影像。我们看见摩天大楼或飞行中的飞机爆炸,人的身体被炸碎。我们恐惧度日,害怕明天就轮到我们。我们都晓得这种事是丑的,不仅道德上丑,肉体上也丑,因为这种事勾起我们的恶心、恐惧和憎厌——而同时,它们也能撩动我们的同情心、义愤、反抗的本能和团结心,即使我们学某些人相信生命不过是充满喧嚣盲怒的白痴故事,带着宿命主义接受这些丑事。我们再深知审美价值是相对的都改不了一个事实:在这些情况里,我们看见丑事,都毫不犹豫地明白那是丑事,我们无法将之化成喜悦快感的对象。你可以说艺术的声音是边缘性的,但艺术提醒我们:尽管一些形而上学家满怀乐观,但有个无法改变的令人难过的事实——这个世界里有个恶意的东西存在。

《突变第三型》,约翰·卡朋特(导演),1982

《战争之惨》,卡洛,1633

德拉库拉木桩插小孩,1476-1477

《茱迪丝割下荷洛芬尼斯的头》局部,卡拉瓦乔(意大利,1571—1610年),罗马,国家古代艺术博物馆,巴贝里尼宫
本文自:陈衔说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

注:本站部分文章及视频来源于网络,如侵犯到您的权利请联系我们,我们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