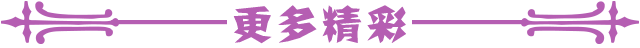一切将从这个命名开始——“啊,我们”。
谁是我们呢?我们是那些画中的人物吗?站在我们的主体位置上,这些画中之人,应该是他们吧,不,“他们”就是我们,或者说,他们不是客体,他们,其实就是曾经的“我们”。
在这个系列组画的开端,余友涵用了一句领袖的著名诗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作为题目,就把画中的“我们”安放到一个《沁园春·雪》的时空框架里,也使得画中的“我们”获得了某种领袖视野的定位——他们是创造历史的风流人物所定义的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1997,90×110cm×5,丙烯,布,图片来源于艺术家
因此,“我们”是人民……
1950年代是人民的创世纪,其最显著的遗传标记是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穿着民族服装的歌舞演员,还有勤劳朴素的英雄人物……然而,他们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甚至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于“他们”的时空之中,另一个起始于1980年代的时空重新定义了“今朝”的时序,时空的“改朝换代”也使得画中的“我们”从人民的物种改变成了众生的属性——他们是时装模特、乡镇仪仗队,是上海郊区的勤劳致富的三代同堂的家庭。当两个时空交汇于一体之时,画中的“我们”如同实现了时空穿越——他们既是人民;也是众生,是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
兵马俑,却在超越“今朝”的另一个时空中凝望着我们,星罗棋布、辰宿列张……俑本是一种代替真人殉葬的替身偶像,“他们”一被烧制出来,就被深埋于地下,供死者的灵魂所享用。所以,俑对于真人的仿真,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技术要求;更是一种让真人相信死者世界与生命世界共通的证据。依照俑的原义,“他们”一旦被埋藏,就会在死者的世界中复活,而永无可能再度凝望生者的世界,除非“今朝”的考古学家把它们从地下挖出来。
因此,余友涵笔下的俑,并非是在今天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兵马俑——“他们”是凝望“今朝”的“我们”之先祖,透过“俑”之于我们的对视,我们从俑的面目和表情上看了“我们”。也许,兵马俑一直都是在那个地下的阴间世界里守护“风流人物”的人民,当“他们”被余友涵唤醒并拉回到这个“今朝”的阳间世界里,并不是他们复活了,而是一种昭示——因为地上“今朝的我们”本来就是地下“旧朝”的子孙后代。在这个意义上,余友涵是一个社会考古学家,他划破了社会的表皮,打开了今朝社会的地层,显现了被埋藏在地下的“我们”,这不是一个异灵的世界,这是一个曾经被过去的“我们”所构造的世界,或者,他们显现了一个“我们”曾经这样被构造的世界观。

《橘黄的兵马俑》,1998,112×112cm,丙烯,布,图片来源于艺术家。
如此说来,从俑的象征意义来看,这些有着明确的年代标记的今朝人物,仅仅只是已经消逝年代的祭品——是一种“时代之俑”。余友涵描绘他们,就像古代的工匠在制造献祭的陶俑,古代的陶俑是为了顶替活人去服务于阴间的主人,在特定的信念中,俑虽然是生命世界的偶人,却是死亡世界的生者。不过这恰恰不是余友涵的意图,他所创造的“时代之俑”,只是用他们的人形符号来标记过去的时代,这一存在于人的记忆中的时间关系,借助于他们的符号之形而被再度激活。
被余友涵激活的时间关系再次提示我们注意,没有时间,除非人的记忆编织了时间的丝线。余友涵使用了黑白与彩色这两种记忆的丝线,编织了多个时空关系的罗网——一方面,30年代的旗袍女人、50年代的少先队员,80年代的时装模特,这些人物就像符号的丝线一样把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编织成了一个符号之网,从类比的角度来说,社会集体的记忆就是一只无形的“意识之蛛”——它吐出无以计数的记忆丝线;另一方面,这些如同涂鸦一样的符号却并非是随意而为的,红领巾与时装模特、跳着葵花舞的演员与搬东西的男女农民工,米兰大教堂与中国式庙宇、中国石狮与佛像,兵马俑与笑容暧昧的女人,如此等等,这些标记不同年代的人物符号被社会集体记忆的丝线缠绕着,如同被捕获的昆虫,他们在记忆之网中扑腾闪跃,但是,却再也无法飞回那些本属于“他们”的时代黑洞了。

《啊!我们之一》,1998,220×300cm,丙烯,布,图片来源于艺术家和香格纳画廊
是余友涵的“记忆之宫”使他们化身为“时代之俑”,变成了与我们对视的“啊,我们”。余友涵的个人记忆重新编织了这一张社会历史的蜘蛛网,也像是一张历史的草稿纸,涂满了草率的年代标记。有时候,这些画面又像是展现了一个大脑内部的意识舞台,它们是梦境的片段,只有闭上眼睛,你才能看见这些画面;当你睁开眼睛之时,这些画面,如同鬼影憧憧,令人惶惑或惊恐。

《黑色绘画》,2000.6,227×182cm,丙烯,布,图片来源于艺术家
余友涵描绘的画面,是一种符号的画谜;也是一种视觉的哑语——表面上看,他描绘的无非都是众生的日常生活罢了,这些碌碌之辈总是在无常的命运中追求长寿,这是集体性保健体操的由来;众生们祈求福禄双全的愿望,成就了信仰的精神仪式,化成了保佑众生的宗教……但是,转换到隐喻的层面上,画面中的人物,又像是逝去的历史派出的接头人,不断地发出暗号,以表明他们的身份,这对于与余友涵同时代的人而言,一定会唤起似曾相识的情感与怀念;不过,当你若是想与画中人物接上头并交换“情报”(情感与报应)之时,他们似乎又隐瞒了什么,他们的面目要么是模糊不清的;要么是摇摆而躲闪的,总之,你肯定不会从他们身上取得一份有真实价值的“历史情报”,不过,你对待历史的情感恐怕就要招来报应了,这一相悖的现象似乎从语义学上揭开了“情报”与“报应”的关系。事实上,无非如此吧,他们,不过只是一些从余友涵回忆过去时代的“记忆之宫”里爬出来的符号灵魂,余友涵召唤他们,于是,他们如同泥偶或陶俑一般现形,漂荡在记忆的天空之下。

《站桩》,2015,130×160cm,丙烯,布,图片来源于艺术家
啊,我们,从俑的象征形态上,我们,已经成为那个早已逝去的时代的殉葬品,那些余友涵的画中人物——这些“啊,我们”,啊,他们,其实是在为那个创造了他们的时代招魂,他们—我们,就漂浮在这个大都市的上空,与今天的时代如影随形,而我们的凡夫肉眼却看不见他们,盖因为很可能他们就是从我们身上分离出来的——“啊,我们”

注:本站部分文章及视频来源于网络,如侵犯到您的权利请联系我们,我们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