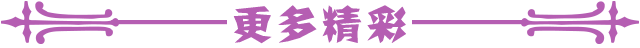德勒兹的困难的核心肯定就在于此。一开始,他似乎在用一种多样性的水平的世界去对抗相范型和复制品的二元垂直世界。他似乎在用这如百衲衫一般的独特计划去对抗那在唯物主义和关于优雅动物或对称建筑的唯心主义之间撕扯的、矛盾的作品。他似乎在用蜜蜂为植物授精,以及所有植物和精神分裂的无辜,来对抗亲缘关系模型及其摹仿和过错。但这关于两个世界的图像的简单对立马上就被挫败。这不是在示例性绘画所带来的多样色彩中消溶形象,相反是将形象钉上十字架,把它在某种矛盾的冲动中建造起来,这一冲动所指向的正是图像去形象化这一充满矛盾的工作。文学文本同样如此:在这里并没有无序的、存在的个体性去充填它,相反却过于自信地专注于这些揭示了其实际意义的特异者的英雄形象上。我说过,德勒兹想用一块地基取代另一块,用经验论者的英国地基取代德国观念论者的地基。然而,这些看似令人惊奇的、朝向粗糙叔本华主义形而上学的以及某种对文本的直白的象征主义解读的回归,也同时表明了某些力量会挫败这个简单的取代;多样性的植物的无辜被取代了,一个由模范性人物所指引的、挣扎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新的形象被强加了进来。
当然,这不是不一致性的问题。要理解德勒兹主义诗学表面上的矛盾,我们必须重建一种赋予文学以政治功能的中介的秩序。小说里的人物同时也是一种召唤那将到来的人的许诺。这一政治赌注恰恰铭刻在文学的事业中,被镌刻在无偏好的原则中。每一个主体的平等价值,将一切关于再现的等级还原为生成的伟大的平等力量,这些将文学与平等缠绕一起。但是,确切地说,这是哪一种关系呢?为文学革新奠基的分子平等,与政治共同体能够实现的平等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是福楼拜,为这个问题给出了经典的公式。对他而言,政治平等属于幻象的秩序,表象性的意见(doxa)秩序。它们不可能改变等级,不可能达到另一种关于统一的叙述。人类的个体并不是平等的原子。在他给科莱的著名书信中说的:“如果我不像朝向乞丐一样亲切地朝向叮咬着乞丐的虱子,魔鬼就会把我带走。此外,我确定人不比木头上相像的树叶更多兄弟:他们一起担心,仅此而已。我们难道不是宇宙的流溢造出来的吗?[...]有时在盯着一块碎石、一只动物、一幅画之后,我觉得我进到了里面。人类之间的交流远没有这么强烈。”[20]
这就是文学的形而上学所固有的政治。这种政治把人类诸个体在社会中的平等,引向一种更伟大的平等——一种比贫民和工人要求的平等更为真实、更为深刻的本体论的平等。这种平等仅仅在分子的层级上进行统治。在友爱的伪装背后,是一种同情将宇宙的纤维连在一起。或者用叔本华的术语来说,有一种怜悯,它是作者所独有的情感,因为它超出了人类诸个体之间关系的秩序。[21]海内皆兄弟这一共同体并不具备本体论的一致性,也不享有任何超越古老的,以父子血缘建立其的共同的之上的特权。
而这种反兄弟友爱的平等,是德勒兹所拒绝的。文学创造的人不能被还原普遍本质的局部情感的表达。分子革命确实是一项友爱原则。不过,分子平等并不是通过它直接的情节发展来实现那种文学来说是独有的东西,并且建立了友爱秩序的。我们必须将文学的伟大创造——自由的、间接的话语——由福楼拜的寂静无为中夺走。在作者眼中,福楼拜并没有建立起来诸主体的平等,相反压制了虚构的力量。自由间接话语所体现的不是风格的绝对观点;而是再现的实际的对立面。这并非原子无差异的音乐,而是杜撰:“当他自己开始‘虚构’的时候,当他进入‘传奇的犯罪现场’,并从这里开始发明他的人物的时候,他正在成为那个实际的人物”。[22]分子革命并不引向那种由作者的全能所给予的、鲁奥(PereRouault)的女儿和哈米尔卡(Hamilcar)的女儿之间的那种平等,但它引向了库德雷斯岛(IleauxCoudres)的农民所使用的虚构的力量。这些农民在电影人佩罗(PierrePerrault)的唆使下,“复兴”了他们传奇的海豚捕捞,由此建立了“魁北克的自由的、间接的话语,一种两个头、甚至千个头的语言”。[23]德勒兹主义的话语中似乎存在的矛盾——被赋予神话人物的特权——于是被消除了。杜撰的人物(无论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才是反再现主义的最终目的(telos)。“杜撰(fabulation)”才是虚构(fiction)的对立面。它是艺术创造和生命力量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你会注意到,通过对照另一种艺术,即电影,德勒兹将这一观念阐述得更为清晰。那种被称为(根据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电影真实(cinéma-vérité)”的形式,非常有助于将艺术的力量转向进行杜撰的和被杜撰的(fabulating/fabled)的人们。与之相比,文学的作用更接近中介。它加入了抵抗的战斗,揭露再现的权力实质上就是大写的父权。德勒兹那些看似矛盾的,聚焦在“英雄”上的分析事实上关注的是那些必须造就一个共享的杜撰和一个全新的友爱的人类的神话性的战斗。德勒兹所赋予特权的故事不仅仅是文学工作的寓言,还是这场伟大战斗的神话,一个战胜了父系共同体的友爱共同体的神话。特异者不仅仅体现了一种文学的生产,他们还是摧毁父系共同体这一范型与复制品世界的神话人物。他们令“另一个世界”的力量同摧毁这个世界的力量一起生效。像亚哈这样的偏执狂体现了父亲的形象,他宁愿走向因过度而导致的自我毁灭。像巴特比和比利·巴德(BillyBudd)缺乏意志的存在,以同样的过度,事实上否定了作为儿子服从的形象。他们以激进的无偏爱(non-preference)来辨认和穿刺。特异者的悲剧由是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一种谨慎的瓦格纳戏剧的面目解放了一种可能性,它是关于那些缺乏品质的人(杜撰者,说谎者,拥有错误力量的人,而这最后一种人被称为真理)的可能性。通过摧毁居于再现体系核心的、父亲的肖像,它打开了一个通往友爱的人性的未来。因此,它带来一种转移,类似基督教旧约到新约的转移。“巴特比不是一个病人,而是病入膏肓的美国的医生,新的基督,我们全部人的兄弟。”[24]
德勒兹看到的这一友爱的未来开始于另一部梅尔维尔的小说,《皮埃尔,或歧义》。在这故事里,友爱与乱伦集于皮埃尔一身。皮埃尔是死人的嫡出儿子,伊萨贝拉则是庶出的女儿。当然,我们可以顺便再次召唤出瓦格纳还有黑格尔的《安提戈涅》分析。在《安提戈涅》中,兄妹夫妇作为精神力量似乎居于家庭的真正核心。而巴特比的整个文本可以视作黑格尔讨论希腊悲剧的一段移置过的自由评注。不过,重要的地方不在于重新刻画德勒兹的“美国”剧本压制的德意志与希腊阴影,而在于观察这一剧本如何连接两段故事:原罪或父系秩序的原始破裂的故事和一个对父系秩序一无所知的无辜的友爱世界的故事。
事实上,在“巴特比或句式”中,美国乌托邦可能是——或可能已经是——伟大的友爱希望的另一种图景的呈现:与无产阶级的世界相对的同志的社会;另一种伟大的希望,虽然也被没收了,可能性却还是这么丰富。这一乌托邦与苏联的乌托邦截然相反——那一乌托邦在外部被父系的形象吞噬殆尽。美国革命不仅与英国父亲决裂,同时还阻档了后者的权力,实现了一个没有父子的社会,一个由同行兄弟组成的、没有开始和终结的小型国家。这一革命建立了一个少数派的国家,其小说拥有卡夫卡这一布拉格的德裔犹太人所运用的少数派语言的或语言中的少数派的力量。[25]德勒兹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友爱美国的哲学:另一种文学形而上学围绕着詹姆斯兄弟(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建立起来。假设这一美国存在,我们会奇怪是什么让梅尔维尔预言了这一国家的存在。然而,德勒兹的选择与之截然不同:如果我们忘掉由梅尔维尔的小说以家庭大屠杀为终结,那么关于皮埃尔和伊丽莎白的乱伦小说,事实上精确地再现了两种在根本上相互冲突的小说所相遇的那处坐标:一出关于亡父和原罪的戏剧,与一个关于土著的神话,一出兄弟姐妹在从未有过父亲存在的世界中漫步的戏剧相交的那一点。观察这一由此书而来的矛盾如何连接在一起是可能的。在德勒兹的分析中,有一本书扮演了向导的角色,这一向导时隐时现。我指的是劳伦斯(D.H.Lawrence)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ClassicAmericanLiterature)。[26]
劳伦斯此书的意图在于由美国文学中摘取出还笼罩在双重迷雾中的新世界的真正秘密:对唯心主义纯粹性的梦想,仍然封缄在欧洲和基督教的父子关系的宇宙中,它随后转向一种对于无辜的、友爱的民主的自由之梦。梅尔维尔和惠特曼这两位作者完成了这一循环,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两种梦想用象征呈现了出来。梅尔维尔刻画了一个投身于理式的十字架的男人,处身于载满理式的疯子的船上,狩猎着仅凭鲜血和直觉活动的生物,最终被这一生物摧毁。惠特曼则刻画了一个超灵论(unanimist)的梦想,赤裸灵魂的民主。这一灵魂游荡在高速路上,除了游历外没有别的目的,除了与生俱来的在道路中辨认自身的能力,也没有其他的社会性的形式。
不过,读劳伦斯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张力在抗拒着前两人那种直白的神学。在劳伦斯对惠特曼这一异教徒伟大之处的体认中,夹杂着一丝嘲讽,以及同梅尔维尔这位基督徒的某种秘密的共鸣。他在惠特曼那里看到了未来的讯息,同时他注意到了惠特曼的双重局限:一方面,他对他同道的爱还是将同情,将共感的力量封存在旧的唯心主义的慈善中;另一方面,他天真地以为友爱可以马上实现,我们可以马上摆脱邪恶和罪恶。而梅尔维尔,曾经直面怪物的人,似乎肩负了某种更卓越的艺术的力量,也即更卓越的真理的力量。劳伦斯想要呈现的美国真理类似于一个将梅尔维尔的理性内在化的惠特曼,他将那同天使和野兽角力的唯心主义力量交还给民主的同情。
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德勒兹告诉我们的。他召唤出了一个友爱的美国,通过在亚哈或克拉加特(Claggart)之间的不朽的角力,他们将会打落“父亲的面具”,在原始自然的特异者和普通人类之间达成和解。不过德勒兹似乎通过颠倒劳伦斯的逻辑,将这种张力消解掉了。他给了梅尔维尔以惠特曼的理性,他将巴特比这一主动的遁世者变成了美国开阔大道上的英雄。他把皮埃尔-伊丽莎白这一对变成了同志社会的创始人,他把梅尔维尔变成了美国的代表——这个美国从一开始就期盼着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共同体。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劳伦斯面对这样的美国图景时会有怎样的讽刺。在这里,德勒兹旨在再次建立文学的一致性,建立文学创造的人物的一致性。这个问题是关于如何在文学的断裂中展示那种从父权社会,以及其同构的表象的世界所决裂的激进的端裂。但这通过压力而制造的一致性似乎马上就乱做一团。德勒兹歌颂灵魂伟大的自由之路。是啊,我们怎么能不为他所描述的那个“在过程中,群岛的”世界的图景所振奋呢?这个世界属于友爱的个体:“一堵由自由的、没有用水泥固定的石块砌成的墙,其中的每个元素都有独立的价值,但这价值又是通过与其他元素的关系体现的。”[27]我想这是德勒兹最后留给我们的最宏伟、最强大的图景之一。同时也是最奇怪的图景之一。我们知道,“自由的[libres]、没有用水泥固定的”石块,同建基于父之律法的共同体的建筑布局是完全冲突的。然而在一个弥赛亚意味如此明显,且任何其他文本更显著的文本中,为什么那关于一个行进中的全体,一个引领探路者们走上伟大道路的意象,必须是一堵墙?在这里,与建筑秩序或优雅动物相对抗的,不再是植物繁殖的无辜,而是一堵自由的墙,一种意在避开对抗冲突的矛盾修辞(oxymorique)的形象。不过这可能同时给我们呈现了矛盾的终极形象。这一形象是思想的美学模式固有的,也是自律和他律联合体的核心固有的。不过这一形象似乎也阻碍了文学的中介作用,阻止了人们来到共享的杜撰之路上。毫无疑问,在德勒兹看来,有一种友爱承诺的类似无休止的延异(différemment)的存在。他承担了永无止境的自动校正工作,不断修改他提供的思考图景。就像他总是必须将“游牧”(nomade)思想由普遍的运动[mobilisme]中切割出去,不然二者就过于相似了。因为普遍的运动论同样是一种清静无为,一种无差别论。文学在其文本中表明了这一点,而今天占统治地位的意见(doxa)给了我们一副关于它的漫画。在一个统治话语将秩序建立在声称一切事物都在永恒地到处运动且不应被扰乱的断言的时代,德勒兹逆流而行,对这一意见(doxa)提出异议。他在这堵古怪的自由之墙前将我们拦了下来,问题不在于这些石块是如何集结在一起的——时间总会带来这种均衡——而在于他们的聚集如何转变为规范,来表现这个友爱的自由世界。
不过,对我而言,这一自由之墙的悖论不仅仅意味我们需要将游牧思想同它的漫画形象区分开,它同时还呈现了德勒兹的难题,他召唤文学来扫清通道上的障碍,具体的方式则是一劳永逸地刺穿表象世界的高墙,创造友爱的政治的人。这一政治的人由个体而来,由存在论定义的个体的平等模式而来,由其建立的褶皱的存在模式而来。而“自由石块之墙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将我们送回到了“德勒兹的巴特比究竟是谁”这一问题中。把我们从父权律法中解放出来的基督兄弟是什么?这一奇怪的基督,并没有道成肉身,他来自死信(deadletters)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只能看到无人过问的没有地址的信件,或寄到不存在的收件人处的信件。这些信寄给一个父亲-上帝,一个没有手打开信件,没有眼读信,没有嘴谈论;一位聋哑盲的父亲——他以一堵墙将球回弹回去的方式将自己的儿子巴特比送到了这个世界上,让他发出和“肉身化”(incarner)唯一的词组——这意味着,他是一个什么也不喜欢的“好”父亲,精神分裂的父亲。因为他没有任何器官选择事物,因为他的器官,他的嘴、眼睛、手脱落得到处都是,脱落得这个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是,因为他事实上除了脱落什么也不是。
正如我们看到的,问题在于当精神分裂的父亲取代律法的父亲时,其他种类的友爱并未正常地形成,只有原子、原子群,偶然及其不间断的修正。除了差异性的无限权能和无限的无差异的同一之外,没有什么在形成。问题依然在于:人们如何才能在政治共同体中用这一无差异性制造差异?差异必须由一位调停人制造出来,由一个基督般的形象,一个“红着眼睛”从另一边折返,由正义之地折返,由沙漠中折返,且除了无差异性无话可说的形象。之后,调停人必须执行两项而不是一项操作。他必须用存在的巨大的无秩序,用沙漠的正义对抗古老的父系律法。不过,他同时必须将这一正义转化为另一种正义,将这种无秩序变为一个以柏拉图模式构造的正义世界的原则:在这个世界,人类的多样性根据他们的贫瘠来排序。
德勒兹的巴特比,这一基督兄弟,精神分裂的父亲的使者,可以被视作另一位文学人物的兄弟。还有一位哲学家问了自己同样的问题,在前引同一位基督徒的帮助下,他创造了这一文学人物。我说的当然就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德勒兹指控巴特比的正是尼采指控查拉图斯特拉的,这一狄奥尼索斯的使者,基督或敌基督者,被控告宣布了一个唯一的真理。他知道的不是上帝已死这一消息——这一消息只会让末人感兴趣——而是他已精神错乱。在上帝极端的“无偏爱”(non-préférence)这一真理中——我们也可以称这一上帝为生成、存在或本质——形成新的正义原则是有问题的。这种原则被称为“等级制度”,尼采在书写和评注中,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空白处大量提到这一名称,而查拉图斯特拉自己从未发出这一声音。因为要发出这一声音,他必须首先成为能够言说差异和无差异(或永恒复返)的平等的嘴,成为能够造就可以听到这言说的听众的嘴,成为能够同查拉图斯特拉的大笑一道大笑,而不会将它转向与之相反的愚人狂欢节的嘴。在查拉图斯特拉带来的讯息里,“正义”的未来存在于切断在查拉图斯特拉关于“超人“的美学教育,同人们将之搬演成为的喜剧(“愚人节”,或者,可能非常简单的“查拉图斯特拉主义”)之间的联系的必要性中。同时,它又是不可能被切断的。在此书的概念中,关于在本体论和政治之间的通道的难题,被标记为终结问题的悬而未决。尼采有一个构思好但的未成文的结局,它告诉我们查拉图斯特拉是一位建立其等级制度的立法者。在1884年出版时,此书的结局以“第五福音”的七个印章的结束。然而,还有偷偷印了四十册的第四卷,此卷通过刻画“超人”上演的“尼采主义”喜剧,重启了印章。[28]
这确实是一项与查拉图斯特拉的使命平行的使命,一项扫清本体论与政治之间的通道的使命,德勒兹将这项使命托付给了作为普遍性的文学和作为个别性的巴特比。德勒兹的正义确实处在尼采的“等级制度”最远的延长线上,名为友爱。接下来,问题在于如何清理在疯狂的上帝那平等的贫瘠的正义和友爱之人的正义之间的道路。德勒兹告诉我们,这件事必须被视作一场喜剧。文学是一场喜剧,给了我们疯狂上帝的巨大笑声,为行路人的友爱清理出了道路。但是这一喜剧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喜剧一样有着两面性。在巴特比的面具下,德勒兹为我们开辟了同志的开放之路,摆脱了父系律法之后的大众的开怀大醉之途,特定的“德勒兹主义”路径——这一“主义”可能仅仅是德勒兹思想的“愚人节”。但是这条道路将我们引向了冲突:自由石块之墙,无路之墙。我们没有从关于存在的五花八门的咒语走向任何政治正义。[29]文学没有给德勒兹的政治打开任何通道。不存在任何狄奥尼索斯的政治。这一堵墙可能像其石块一样自由。在这堵墙前,狄奥尼索斯这一哲学孩童的欢乐也必须却步了。复仇,或许是来自老欧里庇得斯的复仇,遭到了尼采的唾骂。他确实预见了这些哲学家:狄奥尼索斯不想要任何哲学门徒。他不爱哲学家,只爱愚人。基督对狄奥尼索斯也进行了复仇。兄弟的形象还是呈现为基督或巴特比的形象,呈现为调停者的形象——如果那不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形象的话。而这一自由石块之墙就像那些五彩的彩虹,像那些查拉图斯特拉必须投向未来的空中桥梁一样,冒着被巫师和傻瓜仿制的危险。不过,当然,一种强大思想的强大之处也在于其拥有修复自身难题的能力,特别在无路可走之处。这确实就是德勒兹在这里做的,用同一个手势,他清扫了德勒兹主义的道路,并将其送到了这堵墙面前。
--------------------------------------------------------------------------------
[20]LetterfromFlauberttoLouiseColet(福楼拜与科莱的通信),May26,1853.
[2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鲁斯特在写给贝尔(EmmanuelBerl)的一封信中将其与友爱作比,在此信中他明确提到叔本华。Correspondance(《普鲁斯特通信集》),Paris:Gallimard,Vol.XV,pp.26--28.
[22]GillesDeleuze,L'Image-temps,Paris:Minuit,1985,p.196.谢谢贝卢尔(RaymondBellour)在1997年路萨斯(Lussas)的国际纪录片影展(étatsgénérauxdudocumentaire)上通过将其作为一个项目的主题而让我注意到了这一文本的重要性。[英译注]TranslatedasTheTimeImagebyHughTomlinsonandRobertGaleta,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9.[中译注]中译见德勒兹:《时间―影像》,谢强、蔡若明、马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页238。
[23]Op.cit.,p.197.[中译注]中译见德勒兹:《时间―影像》,前揭书,页238。
[24]Critiqueetclinique(《批评与临床》),p.114.[中译注]中译见德勒兹:《巴特比,或句式》,前揭书,页191。
[25][中译注]参德勒兹:《卡夫卡》,见于德勒兹:《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
[26][中译注]中译见劳伦斯:《劳伦斯论美国名著》,黑马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7]Op.cit.,p.110.[英译注]Cf.p.86intheEnglish.[中译注]中译见德勒兹:《巴特比,或句式》,前揭书,页183。
[28][中译注]关于此书及其出版情况见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编者说明部分,黄明嘉、娄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9]在此处引用巴丢对德勒兹思想的解释时,我由伟大的尼采主义者福尔(ElieFaure)的“关于电影奥秘的介绍”(L’Introductionàlamystiqueducinéma)处借来了这一表达。Deleuze:Laclameurdel'étre(《德勒兹:喧嚣的存在》),Paris:Hachettt,1997.[英译注]TranslatedasDeleuze:TheClamorofBeingbyLouiseBurchill,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00.
本文根据黄锐杰译《朗西埃:德勒兹、巴特比与文学句式》,再行编校复译而成,原文载《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法)雅克·朗西埃著,朱康、朱雨、黄锐杰译,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年01月。
雅克·朗西埃

瓦雅克·朗西埃(1940-),法国哲学家。主要领域有存在学、知识论、伦理学、美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前任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早年即与阿尔都塞合著《读资本论》。80年代先后以“哲学教育”、“历史性”及“诗学提问”的研究著称,90年代初开始整理其自身的理论系统,专注于美学-政治的研究上,提出“歧论”。

注:本站部分文章及视频来源于网络,如侵犯到您的权利请联系我们,我们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