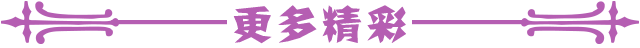图1 莫特利 骑师俱乐部 布面油画 66×81.3厘米 1929
数十万美国非裔人口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13—1945)离开南方乡村,移居至北方工业城市,史称“大移民”(the Great Migration)。实际上,自19世纪80年代就陆续有黑人从南方前往北方,这种趋势到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时发生井喷式增长。美国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将大移民归纳为“排出”及“纳入”的结果。所谓排出是南方黑人所面临的负面因素,例如私刑与严苛的种族隔离。而纳入是北方在这一时期所呈现出的使黑人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种种可能:广阔的就业前景、受教育的机会、更为宽松的生活环境等。〔1〕虽然与南方相比城市生活意味着更多的自由,但非裔美国人还是因为种族隔离等原因而被动选择了聚居生活。一战后,纽约、费城、芝加哥、波士顿和底特律等城市的黑人社区迅速壮大。以纽约的哈勒姆区为例,在1924年已有超过15万非裔人口。〔2〕这些非裔社区常常因规模庞大而被称为“城市中的城市”。
另一方面,法国巴黎成了一战后非裔美国人在海外的热门移居地。自19世纪下半叶起就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漂洋过海来到法国。而到了20世纪,非裔美国人赴法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大移民浪潮的外延。法国对于非裔美国人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不外乎更多的自由与更为宽松的种族氛围。法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以及越来越便捷的跨大西洋航线也促使许多非裔美国人移居法国。〔3〕巴黎在一战后形成了以蒙马特为主要代表的非裔社区。而与纽约等国内城市不同的是,巴黎非裔社区的形成并不是非裔侨民的被动选择,而是基于他们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共同纽带。
随着聚居式都市生活越来越多地成为非裔美国人共同的现实经验,这一时期也有许多非裔艺术家专注于这一题材的视觉呈现。其中既有城市生活赋予黑人十分积极的一面,也偶尔映射出非裔社区与母体城市的差距与隔阂。在这个过程中,非裔艺术家不仅仅是在捕捉和描绘非裔社区的街道、店铺、如织的人群以及街上的霓虹,而是在表现美国黑人群体在获得自由身份半个世纪后,正在为他们自己,也为整个美国社会提供一种新的被观看的方式。描绘着都市生活的非裔艺术家们是这一过程的观察者,同时也是参与者。
异域——在巴黎的非裔美国人
美国非裔文化最先在巴黎被人熟知的方面是他们的爵士乐,这种常常被一战非裔士兵演奏的音乐很快得到了巴黎人的认可,并被扩展为对于非裔美国人的喜爱。在20世纪20年代,巴黎市中数不清的夜总会和俱乐部中都希望演奏这种崭新的、富有节奏感的音乐。非裔爵士乐演奏家在巴黎炙手可热,他们在这里可以赚到比纽约和芝加哥高得多的薪酬。巴黎北部的蒙马特在当时成了非裔侨民的聚集地以及黑人爵士乐的中心。这一地区曾以印象派画家而闻名,到了20世纪,蒙马特高地的艺术吸引力被蒙特巴纳斯所取代,这里随即转变成了巴黎夜生活的中心,也是当时最著名的夜总会——红磨坊的所在地。同样作为一个大城市中的黑人生活区,蒙马特与纽约的哈勒姆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富裕的黑人侨民租住这里的房屋,而经济条件较差的人则选择住在廉价的旅馆。不演奏爵士乐的黑人常选择居住在蒙马特之外,但依然会被这里的餐馆和夜间的酒吧吸引。
除了生活惬意的非裔社区外,巴黎的世界级美术馆与佳作、让人眼花缭乱的展览以及在一流艺术院校就读的机会也让美国非裔艺术家们向往不已。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在巴黎已经获得显赫声望的亨利·奥萨瓦·坦纳,还有多位青年非裔美国艺术家在巴黎学习和生活过,其中包括格温多琳·本内特(Gwendolyn B. Bennet)、艾伦·道格拉斯(Aaron Douglas)、威廉·E·格兰特(William E. Grant)、帕尔默·海登(Palmer Hayden)、威廉·H·约翰逊(William H. Johnson)、阿齐巴尔德·莫特利(Archibald Motley)、伊丽莎白·普菲(Elizabeth Prophet)、奥古斯塔·萨维奇(Augusta Savage)、劳拉·惠勒·华琳(Laura Wheeler Waring)、阿尔伯特·亚历山大·史密斯(Albert Alexander Smith),以及黑尔·伍德鲁夫(Hale Woodruff)。
1928年,成长于芝加哥的非裔艺术家莫特利在纽约的新画廊(the New Gallery)举办了个人展览。在展览图册封面上的宣传很好地诠释了这次展览对于莫特利本人以及所有同时代的非裔艺术家的重要性:“纽约画廊为黑人艺术家举办的第一次个人展览毫无疑问可以写入美国学院绘画的历史,这是一个代表着明显艺术趣味的事件。然而新画廊对于莫特利先生的这次邀请或许拓宽了所有人对于他以及他的血统的认知,这一切只因他是位卓越的艺术家。”〔4〕展览得到广泛关注,《纽约时报》也做了大幅报道,对于一位非裔艺术家来说,这象征着极高的赞誉。展览中包括许多莫特利20年代展创作的表现黑人的肖像画作品,一个值得一提的对比是仅仅在几年以前,莫特利还曾因向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年度展览提交了一幅表现黑人的作品而遭到另一位非裔画家威廉·法罗(William Farrow)的劝阻。莫特利称当时他的许多非裔艺术家朋友“十分害怕向任何展览提交关于黑人的作品”。〔5〕然而,在1928年的展览展出的26幅绘画作品最终售出22幅,成绩斐然。很快,莫特利又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供其赴巴黎学习。
在1929年夏天到达巴黎后,莫特利很快投入到了一种全新的创作尝试中。《骑师俱乐部》(图1)是莫特利在巴黎创作的第一幅作品,作品中的场景距离莫特利刚抵达巴黎时所居住的伊斯特利亚酒店仅几步之遥,同在蒙特巴纳斯大道上。骑师俱乐部是一间夜总会,经营者曾经是一名骑师。该夜总会还有另外一位主人,美国艺术家希拉瑞·希勒(Hilaire Hiler)。希勒与多位旅居巴黎的美国艺术家熟识。〔6〕自1923年两人开始经营骑师俱乐部开始,这里就变成了巴黎夜生活的热点之一,马克·吐温曾称赞这里是“有史以来最棒的夜总会”。画家着重地强调了它极受欢迎的事实,因为无论用什么方式观察这件作品,观众的目光似乎都无法避开骑师俱乐部那显眼的招牌。形形色色的人在这家俱乐部的周围停留或走过,共同构成了这巴黎夜生活的一角。而人群中最为显眼的是站在门口穿着红色礼服的黑人门童。他斜倚在入口旁,右手插在兜里,左腿绕在右腿上,以至于他的整个重心都偏向他的右侧,看上去有些滑稽。他在向人群中的某一位——或许是这里的熟客——笑着,露出了他与肤色形成明显对比的洁白牙齿。学者莱宁格-米勒(Theresa Leininger-Miller)称莫特利将门童放在了画面的中间寓意了他在现实中的位置,“一半站在门内,一半在门外,在(内外)两个世界里,他均不是一部分。”〔7〕尽管这位门童毫无疑问是站在俱乐部的门外,但他的确没有如其他人一样成为享受巴黎夜生活的一部分。虽然他在见证着这样一个过程,他却并没有投入其中,而只是一个局外人。
画面使用了对比明显的色调,路灯、车灯以及牌匾上的霓虹都呈现出温柔的暖色,照亮了画面中巴黎夜色的一部分。在暗部中使用的冷色调更衬托了灯光照亮的地方蕴含的吸引力。巴黎的夜生活如一个舞台,画面中人物都如粉墨登场的演员般自顾自地表演着。同时,莫特利尽量还原这一富有戏剧感的画作中源自现实的细节,例如俱乐部墙上画着的出自希拉瑞·希勒的壁画,描绘的是美国牛仔和美国原住民,也被莫特利完整地用画笔转移到了画布上。骑士俱乐部从某种程度上象征了20世纪初美国艺术家与巴黎的紧密关系,不仅仅是由于俱乐部的老板之一是位美国画家。还因在当时的巴黎有太多源自美国的艺术逐梦者,在非裔美国人心里,激励他们的是亨利·坦纳、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或杜克·艾灵顿(Duke Ellington)。1929年至1930年,莫特利短暂地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分子,却又很快决定返回美国。也许,这幅创作于莫特利刚刚抵达巴黎时的作品准确地反映了画家对巴黎的感受,就如同画面中穿着红色制服的门童一样,虽然身处于舞台中央,但仍感觉自己只是个观看者。
与莫特利相似,帕尔默·海登也在20年代后期抵达巴黎。海登不仅将自身的日常经验放置于作品中,同时他也乐于借鉴他时常暴露于其中的关于非裔美国人的漫画形象,尽管这些形象并不经常显得十分友好。海登生于弗吉尼亚州的怀特沃德,16岁时便离开家乡前往华盛顿,在一家马戏团做杂工,主要负责饲养动物和管理道具。在闲暇时间海登喜欢以马戏团的演员为模特画些速写,他的绘画天赋被一些演员发现,很快他们开始让海登为他们创作宣传用的招贴海报。这一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海登之后的创作风格。招贴画中那直接的、简洁的处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在海登的作品中找到。〔8〕1926年,他的作品《布斯贝港》赢得了该年度哈蒙基金会艺术金奖,这也是哈蒙基金会第一次举办全国范围的艺术评选。随后他又得到了白人慈善家埃利斯·戴克(Alice Dick)资助的3000美元奖学金,通过这笔不菲的捐赠海登得到了去巴黎的机会,并在那里学习了5年。

图2 帕尔默·海登 我们四个在巴黎 纸上水彩 55.5×45厘米 1930
1930年〔9〕,海登创作了水彩画《我们四个在巴黎》(图2),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描绘了包括他自己以及好友黑尔·伍德鲁夫、作家康梯·卡伦(Countee Cullen)、医学院学生恩内斯特·杜普雷(Ernest Dupres)在内的四人打牌的场景。通过赋予画面一种荒诞性与不和谐,海登的作品中呈现了带有其个人风格的滑稽叙事。四人围坐在一张正好容纳他们的小牌桌旁,远处的另外两名黑人在玩着桌球,这是当时巴黎许多咖啡馆常见的娱乐设施。值得注意的是,打牌的人们却完全没有将注意力放在手中的牌上,而是被其他的事情所吸引而好奇地望去。而他们又明显被不同的事情分散了注意力,因为靠近画面左下角的两人与另外两人望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美国非裔艺术家艾伦·道格拉斯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借鉴过古埃及艺术中的造型手法,即身体的正面像与头部的侧面像的结合(图3)。

图3 艾伦·道格拉斯 为《上帝的长号》作的习作 板上蛋彩 31.8×24.8厘米 1926
海登的《我们四个在巴黎》明显是延续了对于这种借鉴的兴趣。然而与道格拉斯不同的是,海登在这一基础上采用的是更为具象化且滑稽化的表现手法,香肠一样的粉红色厚嘴唇,凸起的下庭以及夸张的鼻子都让人联想到常在漫画中出现的黑人形象。印第安纳大学的副教授芙比·沃夫斯基尔(Phoebe Wolfskill)称海登在作品中的处理不仅受到了长期存在于表现非裔人群中的根深蒂固的模式的影响,同时不能忽略的是海登对于东非艺术的浓厚兴趣。生活于坦桑尼亚与莫桑比克境内的马孔代人创作的雕塑中经常出现类似的形象(图4)。通过对于非洲艺术的多重挪用与借鉴,海登画作中的形象成为共同构建“非裔”或“黑人”整体视觉中的一部分,同时,巴黎现代生活的日常经验与久远的非洲传统也在其中消解为每一个人物身上不可分割的共同特质。

图4 马孔代面具雕塑 木及毛发着色 25.5×29×38厘米 20世纪早期
黑色大都市
1930年,莫特利从巴黎回到了家乡芝加哥。他的作品中开始更多地出现以布朗兹威尔为背景的黑人日常生活的画面。布朗兹威尔区位于芝加哥的南部,与纽约的哈勒姆区一样,是风城非裔美国人聚集的社区。彼时的布朗兹威尔区十分繁华,剧院、餐厅和酒吧林立,被誉为“黑人的波西米亚”以及“黑人的百老汇和华尔街”。尤其当夜幕降临时,布朗兹威尔依然灯火通明,热闹非凡。37街附近是当时布朗兹威尔街的核心地段,这里被称为“漫步区”。〔10〕随着非裔美国人从南方不断迁徙至此,“漫步区”逐渐拓展成芝加哥的“城中城”,这里似乎是独立于外部的黑人世界,有非裔美国人自己的报纸、杂志、音乐、电影甚至是棒球队。虽然“漫步区”成了芝加哥的“黑人麦加”,但阿奇巴尔德·莫特利事实上居住在布朗兹威尔区的边缘,一个白人占多数的社区。莫特利的传记作者艾米·姆尼(Amy Mooney)将他描述为“有着局内人特权的局外人”。〔11〕这种若即若离使莫特利可以站在十分特殊的角度观察并呈现当时的非裔美国人群体。

图5 莫特利 黑带 布面油画 83.8×102.9厘米 1934
芝加哥南部的黑人生活状态在《黑带》(图5)中被莫特利展现了其惬意的一面。自大移民开始后,芝加哥就成为南方非裔美国人迁居的首选目的地之一。虽然哈勒姆区被誉为黑人城市文化的“首都”,但芝加哥的吸引力也毫不逊色,并且这里常常意味着新移民能获得更多的自由。1900年之前,大部分非裔美国人居住在多人种的混居社区(虽然这些社区都集中在城市的特定区域)。1915年后,芝加哥的非裔美国人数量激增,他们很快定居在了芝加哥市南部由18街至39街的一块狭长的街区内,由于在地图上看起来这片黑人社区又细又长,所以被称为“黑带”。在《黑带》所描绘的穿梭于“漫步区”的穿戴时髦的人群中,一位非裔警官在指挥着交通,他虽然站在画面的左侧,但其与众不同的身份依然十分抢眼。莫特利描绘的这个人物准确地呈现了大移民后美国黑人群体的新变化——更为宽泛的职业选择,当然这只是莫特利赋予这幅作品众多丰富细节的一部分。在警官的身前,一个黑人报童看似正在向一位穿着体面的老人推销报纸。芝加哥的黑人出版业十分繁荣,早在1905年,《芝加哥卫报》便已开始出版。作为一份主要针对黑人读者的报纸,《芝加哥卫报》对于黑人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30年代的《芝加哥卫报》已经由周报改为日报,包括兰斯顿·休斯在内的许多著名黑人作家曾为该报撰稿。距离报童不远处,一位职员打扮的中年男子站在几对时髦的青年情侣中间。在他们后方的马路另一侧,有一对情侣在车内拥吻,和他们有着一样肤色的出租车司机正载着这两名乘客缓缓穿过这片繁华的街区。两个青年人有说有笑地走过小酒馆的橱窗,他们的步伐看起来有些夸张。在从私刑泛滥的南方迁至北方都市之后,一小部分黑人十分满足于非裔区给予他们的新状态,同时他们缺失的教育经历使这种满足以并不讨人喜欢——也包括他们的非裔同胞的反感——的方式表现出来,几人结伴操着奇怪的口音大声喧哗并迈着摇晃的步伐在街上踱着是当时常见的景象。这些行色各异的人们尽管来自黑人社会的不同阶层,但他们极有可能是在相似的时间节点来到芝加哥的众多家庭的一分子。这些新时代的黑人在此扎根并茁壮成长。他们尝试新的事物、新的装束以及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城中城“黑带”这个独立于外部的世界中尽情地活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群体式的“隔离”为非裔美国人提供了及时并恰如其分的保护,使在当时的社会无法得到完整权益的个体看到了在此实现大部分诉求的可能。

图6 莫特利 星期六的夜晚 布面油画 81.3×101.6厘米 1935
在《星期六的夜晚》(图6)中,莫特利将他对于布朗兹威尔夜生活的描绘转移到了室内。在一家爵士乐俱乐部里,每个人都看似不可或缺的构成了这随着音乐流动的场景的一部分:一位舞娘在画面中间卖力地表演着,她的位置自然地填补了吧台区与圆桌区之间的空白;距离舞娘不远处的举杯饮酒的男士看起来已经微醺,他对面的女士则悠闲地抽着烟,百无聊赖地望向手中的酒杯;画面后方的乐队在演奏,服务生似乎都配合音乐踱着舞蹈般的脚步为客人服务;吧台的酒保看似早已习惯这样的场景而显得有些无精打采,与画面前景的男士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用力地后倾并用手顶着桌子,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观看舞蹈的视角。画面中弥漫的红色烘托了让人放松的氛围,并使场景中每个人的肤色都看起来十分一致,而实际上在当时的布朗兹威尔区的爵士乐酒吧里极有可能有着各种肤色的客人。尽管莫特利本人并不居住在布朗兹威尔,但他十分熟悉这里的夜总会和俱乐部,他也是第一位选择表现黑人都市夜生活这一题材的艺术家。〔12〕从一个当代视角呈现非裔美国人,夜生活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选择。画中舞女那略显夸张的舞蹈动作以及性感的装扮显示其跳的是时下黑人夜总会中十分流行的林迪查尔斯顿舞,一种结合了林迪舞、查尔斯顿舞以及早期南方农场十分流行的黑人朱巴舞的舞蹈。在30年代林迪查尔斯顿常伴以爵士乐演奏,并以大幅度的摇摆动作而深受人们喜爱。〔13〕在莫特利极具现代主义特征的描绘中,都市的不同片段如舞台的布景承载着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物的自我演绎。他画中的人物形象时常是夸张甚至是模糊的,但又极富代表性。在重置关于非裔美国人视觉经验现实的过程中,莫特利十分坚定地宣扬了都市赋予他们的积极意义。
然而,非裔美国人的“城中城”生活并非总是给人以愉悦,在30年代,城市黑人群体的生活依然受到多重挑战。由于受到公共艺术振兴署资助,海登于1938年创作了《哈勒姆仲夏夜》(图7),在作品中海登刻意强调了哈勒姆区的“拥挤感”。极具哈勒姆特色的楼外台阶上坐满了人,每一处都是如此。一些孩子因为没有找到台阶上的“座位”而只能坐在地上。就连楼上的窗户都挤满了向外张望的黑人面孔。没有了《我们四个在巴黎》中与非洲艺术的紧密联系,海登却更加强调了白人眼中关于黑人和哈勒姆区的刻板印象——简化了的凸显臃肿双眼和夸张下颌的滑稽面孔与拥挤凌乱的社区街道。同为非裔艺术家的詹姆斯·波特(James Porter)在1943年十分尖锐地批评了这幅作品就如“曾经在荒唐可笑的公共广告牌上经常张贴着的宣传黑人歌手的广告”。〔14〕海登对于这种挖苦和指责的回应是自己是在描绘一个时代,他象征性地隐喻了黑人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戏剧化的、严肃的或是令人沮丧的。与波特的评价刚好相反,阿兰·洛克给予《哈勒姆仲夏夜》极高的评价:一个现代主义画家对于现代社会的描述。洛克看到了海登作品中欧洲现代主义观念与海登本人的素人艺术家身份的结合,以及海登对于描绘黑人的过程中使用一种表现主义风格而不是叙述性现实主义的决心。

图7 帕尔默·海登 哈勒姆仲夏夜 布面油画 63.4×76.1厘米 1938
非裔美国艺术史学者沙朗·帕顿则将《哈勒姆仲夏夜》的创作思路归结为对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仲夏夜之梦》的现代化演绎。〔15〕这部莎翁作品中相对少见的喜剧中的人物亦被数不清的电影、大众绘画以及广告等媒介转换成视觉形象,在其中形成刻板守旧的、脸谱化的呈现习惯,而这与白人笔下的黑人形象或长久以来被主流视觉媒介传播的黑人形象的构建过程有相同的意味,这也或许是海登在画中将黑人塑造得更具漫画感并略显“丑陋”的出发点。帕顿同时提到了仲夏夜与基督教的内在联系。北欧地区仲夏节的6月24日同时是施洗者约翰的生日,也是该地区白昼最长的一天。然而实际上英国的仲夏节都选在6月23日,因此6月22日的晚上即仲夏夜(Midsummer Night或Midsummer Eve)。〔16〕英国民间相传在这天的夜晚人们会经历十分奇妙的事情,这也是莎士比亚撰写《仲夏夜之梦》的背景之一。无论如何,海登本人并没有叙述过自己的作品与莎士比亚戏剧的关联,同时也无法证实作品名字中的仲夏夜与画面中远处的社区教堂是否指向了某些宗教内容。一个更为确切的事实是,在《哈勒姆仲夏夜》完成之后,该作品参加了1938年在洛克菲勒中心举行的展览“4000万人的屋顶”。该展览举办的主要目的是对当时不合理的住房条件表示抗议。当时的哈勒姆区是整个纽约市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最主要的原因是黑人常常由于肤色而需要缴付比白人更高的租金,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比白人低得多的工作报酬,种族隔离也使他们无法选择哈勒姆之外其他整体租金较低的街区居住。加上黑人家庭较高的生育率,因此在当时的哈勒姆区,十几个人居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内是十分常见的事。美国三一学院的历史学教授雪莉·格林伯格在其著作中指出当时的哈勒姆区平均每英亩土地上生活着超过670人,同时由于超出常规的人口密度以及黑人群体普遍贫穷且无医疗保险,因此该地区时常传染病盛行。并且哈勒姆区的房屋所有人也很少按常规保养房屋,居民楼常因失修而导致停电或下水道无法使用。〔17〕海登的《哈勒姆仲夏夜》的确反映了被誉为“黑人麦加”的哈勒姆区在30年代的一个不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侧面。大移民的确改变了许多非裔美国人的生活状态,繁荣了美国黑人文化,但无法忽视的基本事实是他们与白人市民在整体生活水平上的巨大落差。恶劣的居住条件是这种落差最为直观的表现之一。尽管莱宁格-米勒称在《哈勒姆仲夏夜》中海登以愚弄他的白人资助者,尤其是哈蒙基金会为主要目的。但画作中堆坐在一起的一张张滑稽面孔与街道上散落着的垃圾或许也是为了提醒黑人精英,哈勒姆区以及整个美国黑人城市聚集区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
聚焦之外
30年代关于黑人非裔都市生活的呈现常常被纽约哈勒姆区和芝加哥的布朗兹威尔所占据了大多数的关注,实际上,在非裔美国艺术家中也有一些人执着地再现着那一年代其他城市或其他社区的黑人生活。波士顿的非裔艺术家阿兰·洛韩·克里特(Allan Rohan Crite)成长于大萧条时期,毕业于波士顿美术馆学院,并在哈佛大学参加过多项课程,这也许源自母亲的影响——他的母亲曾在哈佛大学进修多年〔18〕。克里特试图向人们展现客观的黑人社区状态,并认为哈勒姆区所呈现的以爵士乐与文学为依托的黑人图像十分“异域化”,与他真实经验中的波士顿非裔美国人相去甚远。同时,与莫特利着重强调布朗兹威尔的都市感所不同的是,克里特更愿意将焦点集中在波士顿中产阶级的社区——他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到的真实性的源泉。他将自己的黑人社区绘画作为非裔美国人真正在都市生活中被都市文明同化的样本,并在一段时期内不遗余力地呈现这一样本。在《哈蒙德街上的游行》(图8)中,克里特描绘了在波士顿下洛克希布莉区——当地最主要的非裔美国人社区——发生的一场欢庆游行。他将黑人社区的日常状态移入到一种欢快放松的特殊场景中。一支礼乐队奏着乐缓缓地在非裔社区行进,道路旁边站满观众,画家刻意强调了他们的中产阶级身份,每个人都穿戴得十分体面。画面背景是十分具有波士顿特点的红砖建筑。这件作品源自于画家日常经验的真实记叙,克里特本人就住在洛克希布莉区。奏乐游行是当地十分受欢迎的一项活动,它常常在周日举行,画中的很多细节赋予观者辨认这些信息的可能。例如,画面中的观众都有着时髦的打扮,没人身着制服或看起来像要去上班,更像是刚刚在教堂做过礼拜或观看过一场棒球比赛。人群中的儿童提示了这些活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同时,通过呈现一项发生在黑人社区的文化活动,克里特使观者——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有了从新的侧面观察非裔美国人群体文化身份的机会。画家还刻意使这种呈现秉持文献般的精准,即使这是与克里特自身紧密联系着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图8 阿兰·洛韩·克里特 哈蒙德街上的游行 布面油画 1935
波士顿似乎给予了克里特艺术创作所需要的全部营养。克里特称:“我从小时候起心里就有着明确的想法,我要画自己人,而且就把他们画成他们本来的样子。”〔19〕1936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展览“美国艺术的新视界”,展出的是联邦艺术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选出的在该项目资助下诞生的优秀作品,克里特的《放学》(图9)也入选了该次展览。能够入选全国级别的展览,并与包括托马斯·哈特·本顿和格兰特·伍德在内的艺术家一起展出对于刚刚从波士顿美术馆学院毕业的克里特来说十分难得。《放学》一如既往地呈现出克里特作品中所具有的细微观察与当地特色。作品中表现的是艾弗利特小学放学时的场景。该小学位于波士顿南部,是一所男女生分班教学的学校。女孩们三五成群地走出校门,她们有的彼此交谈,有的则嬉笑打闹着。每个女孩都打扮得十分得体,同时画面中又无法找到穿着相似衣服的两个女孩,克里特保留或者赋予了每个女孩独一无二的个性。她们的母亲也是如此,在温暖的午后阳光中,她们一起享受着日常生活的欣喜瞬间。在画面的远端有几名白人女孩在和刚放学的朋友游戏着,尽管克里特希望精确完整地展示黑人社区生活,但他还是不知不觉地为画面注入了浪漫化的情怀。而无论如何,克里特都用他的方式为30年代的美国黑人社区生活做了十分积极的注解。

图9 阿兰·洛韩·克里特 放学 布面油画 76.8×91.8厘米 1936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赴巴黎学习的非裔美国艺术家大多数选择短暂停留后返回美国,并没有在法国定居。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本土的种族生存环境在20世纪的明显改善,虽然其改善的节奏与程度与非裔美国人向往期盼的有一定差异,但与19世纪末期相比的确有了长足进步。许多非裔美国艺术家赴巴黎的原因是得到更为广阔的、超出自身种族范围的承认,但这种可能性在二战开始前已经在美国本土存在。一战后,哈勒姆文艺复兴在推动了黑人文学与黑人音乐的同时也反哺了黑人美术的发展,而随着大萧条的到来以及“新政”的开始,美国政府对于艺术的大规模赞助随即拉开序幕,非裔艺术家群体史无前例地得到了与白人及白人同行相同的薪资待遇,这极大推动了非裔美国艺术的发展,也从侧面佐证了美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的进步。
非裔美国艺术家在这一时期对于都市生活的呈现客观而全面,既有十分积极的一面,也反映了当时非裔群体在都市中面临的许多问题。这是非裔美国人不断深入参与美国都市化进程的自然选择,在一个类似平行于外部世界的独立的“城中城”中,非裔群体体验着城市给予他们的多彩生活的同时,也需要承受一种全新形式的集体隔离所带来的无奈。尽管在呈现过程中存在角度与观念的差异,但这一趋势适时地替代了之前哈勒姆文艺复兴运动中常常出现的以种族自决为核心的、十分宏大但常常缺乏真实感并无法真实反映非裔美国人生活状态的思潮。通过描绘一个个能引起当代美国黑人共鸣的都市场景——繁华的街头、喧闹的舞厅或是星期天的游行——非裔艺术家们创造了十分详细的多重社会脚本。同时,作为美国美术史中的一部分,非裔都市艺术成为美国艺术为摆脱欧洲艺术的影响而重新探索自身文化定位过程中的关键组成。美国非裔艺术家表现的都市场景与30年代表现典型中西部乡村风格的乡土主义(Regionalism)形成了完整的互补,共同作为美国情景绘画发展的基石和美式现代主义的象征而存在。
注释:
〔1〕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下册),邵旭东译,海南出版社2014年版,第656页。
〔2〕参见Crystal A. Britton, African American Art: the Long Struggle, (New York: Todtri, 2001), 41.
〔3〕关于侨居法国的非裔美国人的资料可参考Tyler Stoval, Paris Noir: African American in the City of Light, (Boston: Houghtton Mifflin, 1996)。
〔4〕原文是“The first one-man exhibition in a New York art gallery of the work of a negro artist is, no doubt, an event of decided interest i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painting. It seems, however, worthwhile to record the fact that the invitation to Mr. Motley to show his paintings at The New Gallery was extended prior to any personal knowledge concerning him or his lineage and solely because of his distinction as an artist.”参见莫特利1928年展览图册的封面图,现藏于芝加哥历史博物馆。虽然原文如此,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纽约的画廊第一次为美国非裔艺术家举办个人展览。1927年,纽约中央车站画廊曾为亨利·奥萨瓦·坦纳举办个展,因此坦纳才是纽约画廊首次为其举办个展的美国非裔艺术家。
〔5〕Robert Bone, and Richard A. Courage, The Muse in Bronzeville: African American Creative Expression in Chicago, 1932-1950, (U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1), 72.
〔6〕参见Theresa Leininger-Miller, New Negro Artists in Paris: African American Painters and Sculptors in the City of Light, 1922-1934, (New Jersey: Rugt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9.
〔7〕原文为“he is part of neither world, standing half inside the club and half outside.” Theresa Leininger-Miller, New Negro Artists in Paris, 149.
〔8〕关于海登的早期经历与作品风格的关联,参见Phoebe Wolfskill, “Caricature and the New Negro in the Work of Archibald Motley Jr. and Palmer Hayden”, The Art Bulletin, Vol.91, No.3 (September 2009), 343.
〔9〕亦有学者认为该作品创作于1935年,参见Sharon Patton, African American A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7。考虑到海登在巴黎的学习时间和经历,笔者认为1930年的说法更为可信。
〔10〕30年代逐渐转移到47街附近。
〔11〕Amy Mooney, Archibald Motley Jr., (San Francisco: Pomegranate, 2004 ); 86.
〔12〕参见Sharyn R. Udall, Dance and American Art: A Long Embrace, (Madison, WI, 2012), 53.
〔13〕参见Jane Dini (ed.), Dance: American Art, Valerie J. Mercer, “The Vicissitudes of African American Artists’ Depictions of Dance between 1800 and 1960”,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207.
〔14〕原文为“one of those ludicrous billboards that once were plastered on public buildings to advertise the black face minstrels”。Sharon Patton, African American Art, 138.
〔15〕Sharon F. Patton, African-American Art,136.
〔16〕虽然绝大部分地区的夏至在6月21日,但北欧地区与英国有着各自的传统。
〔17〕参见Cheryl Lynn Greenberg, “Or does it explode?” Black Harlem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75, 185.
〔18〕参见Edward Clark, Annamae Palmer Crite and Allan Rohan Crite, “Annamae Palmer Crite and Allan Rohan Crite: Mother and Artist Son: An Interview”, Oxford Journals, Vol.6, No.4 Non-Traditional Genres (Winter, 1979), pp.67-68.
〔19〕Richard J. Powell and Virginia M. Mecklenburg, African American Art: Harlem Renaissance, Civil Rights Era and Beyond, (New York: Skira Rozzoli Publications, 2012), 61.
张梦阳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7年第8期)
本文内容版权归本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来源:美术观察

注:本站部分文章及视频来源于网络,如侵犯到您的权利请联系我们,我们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