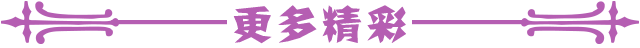当代艺术圈那些事
刘淳 朱其 | 文
人物

朱其
1966年生于上海,博士、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中国国家画院理论部研究员、世界和谐科学院(美国)研究生院荣誉教授、世界文艺复兴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文化复兴基金委员会理事 ;首届世界和谐奖、世界文艺复兴奖评委会评委。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当代美术史专业。新生代代表性的独立策展人与批评家。90年代策划了一系列重要的前卫艺术展,并在国内外媒体上撰写了大量艺术评论和学术论文。曾任《雕塑》杂志执行主编,参与创办"世纪在线中国艺术网",798艺术区艺术总监 ;现生活和工作在北京。
刘淳 :你如何怎样看待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呢?
朱其 :2000年上海双年展及一系列外围展,算是一次当代艺术最后的回光返照,之后当代艺术基本上在走下坡路。尤其是2005年艺术资本介入后,当代艺术开始商业化,进入了格林伯格称之为"前卫的媚俗"阶段。2005年之后,当代艺术整体上呈强弩之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前卫阵营不复存在。
刘 :怎样理解"当代艺术的谎言共同体"?
朱 :即拍卖公司、艺术投资人和经纪人、艺术家形成一个"做局"的联盟,他们操纵价格发布,影响不明真相投资人的市场和学术判断。
刘 :2000年之后,你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以"揭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有人说 :"发生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看见了,但挑破了说出来的是朱其。"我想听听对此你个人的看法?
朱 :那一段时期,我想"捅破窗户纸"。这不是出于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考虑过一旦这么做的所有后果。艺术批评应该将被江湖面子包裹下不好的一面,有勇气摆到台面上来讨论。因为有一部分人利用大家对当代艺术圈的整体形象的爱护,从这个圈子十几年累积的信誉中透支自己的利益。这不仅破坏了当代艺术的前卫生态,并误导了社会对当代艺术的认识。这是我想捅破"窗户纸"的初衷。
我并非一个喜欢冲杀的人。来北京后,我跟哪一派的关系都不深,都是若即若离的,这种角色慢慢会进入一个江湖协调人的最佳位置。但如果以激进的语言"破局"之后,就会失去这个左右逢源的角色,我是想过这个后果的。但我觉得这个"局"别人都不愿破,或者有人愿做但缺乏资历,说了也没人信,也只有我来破了。我的话会有说服力,还会有多米诺骨牌效应。
刘 :你是一位艺评家,同时也是一位策展人。你觉得批评家和策展人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
朱 :批评家不一定是策展人,优秀的策展人一定是出色的批评家。
刘 :在过去许多年里,尤其是在当代艺术批评方面,很多人大概是碍于面子,没有直面一些事情和一些问题,而你却不同,既没有顾忌面子并且直面问题。勇敢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在我看来,你突破了心理的障碍。我想请你谈谈你是怎样放弃顾虑甩掉包袱的?
朱 :在2005年左右,艺术圈一些重要艺术家和批评家违背了前卫精神的底线,与资本共谋利用江湖地位大肆商业炒作,他们是知道在做什么的。艺术批评在底线问题上不应顾及面子,只有将整个事件拖入真实的辩论,艺术批评才能重拾其力量。
在第一届深圳批评家论坛上,水天中先生的发言一直在我的记忆萦绕,他当时说,自己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以前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直到退休了,才有勇气讲真话。当代艺术作为一个从前卫阵营起步的群体,如果连直面真实都做不到,再要往前走超越上一代人,就是一句空话。2005年后艺术资本进入艺术圈之后,当代艺术的阵营分化在所避免,有些人不愿意再前进了。我是一个愿意继续前进的人,但做出正式的"破局"批评之后,需要有被"出局"的准备。当时我作了最坏打算 :从当代艺术圈"出局",回家写小说。我做任何重大决定时,都是想好最坏结果的。
刘 :这几年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事情比较多,用你的话说就是"比荒诞派戏剧还要荒诞,比好莱坞电影还要好莱坞"。听说眼下艺术圈有一句话非常流行 :谁有钱谁就是大爷。这种东西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它是怎么形成的?
朱 :我至今百思不解,一个曾经前卫的群体,突然变成"谁有钱谁就是大爷"的风气,这超出了20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前卫群体的现象。我个人似乎从未担心过以后会穷困潦倒,好像也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倒一直预感自己将来会很有钱。我不是没有感到过金钱在某些时刻的极端重要性,但挣钱不能离精神的核心诉求太远,如果两者冲突,那一切要为精神事业让路。精神是一个务虚的事业,务虚到极致,它自然会将金钱带到你身边的。这是一个人生的虚实转换的辩证法,好像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一点,或明白但不能忍受这个过程。大多数人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诉求,然后一心搞艺术。这种想法看似务实,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只会让自己离艺术越来越远。
刘 :你曾经说过"优秀艺术家的劣质作品",怎样理解这句话?
朱 :20世纪以后,优秀的艺术家成名后会有很多机会,出于应酬、大量的作品销售、频繁地参展,这就使作品生产化,其中必定会产生不少粗制滥造的作品。
刘 :几年前,你曾说过中国当代艺术的"天价做局",由此而带动了整个艺术群体迅速转入商业化。什么是"天价做局"?
朱 :主要是利用拍卖平台搞左手卖给右手的游戏,对社会宣布以天价成交,实际上没有成交,或者成交了但价格不是天价。
刘 :我们有许多批评家,在文章中尽量多说艺术家好的一面而极少说薄弱的一面。后来我慢慢明白,这是批评家在有意保护艺术家,或者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支持一种艺术潮流或艺术现象。但是,后来一些艺术家对批评家善良的保护根本没当一回事情。请你谈谈你的感受。
朱 :批评话语对艺术家及作品"善意的拔高"或"保护性的正面肯定",我自己的批评写作也是有的,比如在90年代对装置艺术、观念摄影、70后艺术的评论。可能原因在三个方面 :1. 批评家想拔高自己推的艺术家或艺术群体的水准,这样可提升批评家自己的学术地位;2. 八九十年代当代艺术还处在边缘位置,需要"唱好"这个群体的形象 ;3. 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同盟关系,或有偿批评的经济原因,也使艺术批评变成"保护性的正面肯定";4. 有些批评家想使批评话语更接近西方理论大师的文风,往往使批评阐释过度。
国内不少知名艺术家实际上没有什么思想,批评对艺术作品的"美化"或"拔高",等于批评家将自己的思想"赠送"给艺术家,那个艺术家创作时并无什么理论观点,后来他却说自己当初就是这个理论观念。我想批评家不必因此心情复杂,重要的是,批评的真正力量不在于人为的提升,而是"叙述事情本来所是的样子"。格林伯格晚年都是如此自省的。

刘 :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一开始得不到主流的支持,于是就通过海外的市场与海外的支持来发展和壮大。等到一定程度之后,名声和社会地位、以及财富都达到一定的高度,同时也受到社会的认可及追捧,于是就开始放弃了原来的态度,放弃了原有的精神立场。其实,他们一开始是通过自己的叛逆来赢得别人的尊重,也通过叛逆赢得所有的一切。但是,他们现在又在极力阻止下一代的年轻艺术家来叛逆和批判他们。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朱 :首先是一种激进后的衰颓症。这批人具体也不尽相同,有的人一开始就把权力和金钱看得高于艺术,可能因为当初无意中卷入前卫艺术,或正好碰上了这个圈子。有些人一开始是理想主义的,后来放弃了理想,这类人又分为两种 :一种可能是认为自己在艺术上已无成为大师或者超越的可能了,索性就享乐主义 ;另一种是生活养尊处优并且钱来得容易,也就形成一路下滑的惰性。其次是一种成功后怕被他人超越的恐惧症。据我所知,这些人成功后精力都花在如何巩固成功地位,并阻止潜在的超越者。
刘 :中国当代艺术,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掺杂着许多混乱的概念。怎样看待当代艺术?
朱 :中国当代艺术要探讨普适性的精神议题,还要重建当代艺术与中国传统的关系。
刘 :有人说,当代艺术是资本的衍生品。你如何理解的?
朱 :艺术品分为两段 :创作中和创作完成后。完成后的艺术品进入传播和市场流通,它可以看作资本的衍生品。在创作过程中,不应把艺术品看作资本的衍生物,否则就是在生产商品,而不是创造艺术。
刘 :早些年,支撑中国当代艺术的是一种批判精神和叛逆意识 ;那么,今天支撑中国当代艺术的又是什么呢?
朱:批判和叛逆仍应是核心诉求,当然,批判和叛逆不仅是指政治和社会层面,也可以是艺术史和语言形式上的。
刘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艺术家以及一些观众相继知道了杜尚和波伊斯,再以后,这两位西方的艺术家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今天,杜尚和波伊斯距离中国观众还有多远?
朱 :应该不是很远了,现在很多白领和新阶层都知道波伊斯和杜尚。
刘 :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时,中国当代艺术虽然处在地下状态,但非常活跃 ;绘画、装置、摄影、VIDIO、行为艺术等应有尽有。我觉得今天反而有些单调,除了绘画——准确点说就是油画和国画之外,其他的种类相对较少。这是为什么?
朱 :市场导向是主要原因,有人购买,就有人生产。
刘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这段时间,我感觉你也在着力推一些年轻的艺术家,或者说你的活动带有推介的动机。后来不知怎么就没有动静啦?是不是市场将你想推介的年轻艺术家淹没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朱 :年轻艺术家过快的市场化是一个原因。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艺术上后劲不足,为人处世上人格不成熟,或发财后不求上进等。
刘 :也有人说你近几年在艺术界的所作所为是在消灭邪恶,我想请你谈谈什么是艺术上的邪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这个邪恶究竟是市场的原因,还是学术的原因?
朱 :从宏观看,这个时代的正邪双方在争夺这块土地,因为中国会影响世界的未来。艺术界当然存在邪恶,比如体制内的人群结盟,控制美院、画院、美协、美术馆等机构,并控制美术史和教科书,将一些二三流艺术家说成是一流艺术家 ;90年代后,当代艺术圈也出现了"邪恶",比如操纵艺术市场、艺术资本、拍卖会、民营美术馆、双年展、画廊、艺博会,甚至编造当代艺术史等。
刘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上有一种致命的东西,就是80后的这一代人缺少甚至没有叛逆精神,没有怀疑精神。我感觉这是一种倒退。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朱 :有一小部分年轻人还是有的,但作为一代人的怀疑和叛逆精神确实消失了。无论是由于政府对主流舆论的控制,还是商业化的市场导向,总之,这两股力量成功地塑造了90年代"去叛逆化"的代际精神的总体性。知识分子对此似乎无所作为。
刘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国内还有民间独立的态度,还有民间独立的立场,然而今天什么都没有了,其实更可怕。
朱 :90年代独立的民间立场,可能是80年代知识分子文化运动的一个惯性,但知识分子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群体存在已被资本和权力彻底瓦解了。

刘 :我曾经看过你的一些文章,对艺术市场进行抨击甚至是揭露。那么你觉得这个艺术市场是在西方的推动下形成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形成的?
朱 :当代艺术市场最早的买家不是西方,90年代初是港台、东南亚,90年代中后期是西方,2000年后中国本土的资本开始强劲介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刘 :我一直觉得,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与主流体系保持一定理性的距离,在相对的孤立中慢慢建树自己,完善自己。可是在今天的文学和艺术中恰恰看不到这一点。我所看到的,都是一种合作,或者叫同流合污。对此你如何看?
朱 :90年代后,由于知识分子和体制处在一种权力的不对称博弈关系,因此,一方面,他们可资博弈的空间不仅狭小,而且受到打压 ;另一方面,体制强大的资本和权力分化并招安了一批原先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这种不对称的博弈状态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刘 :你认为今天的当代艺术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最根本的差异在哪里?
朱 :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艺术品的资本化。
刘 :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说这几年的各种当代艺术展览。各种照片的艺术形式和表现题材大同小异,既找不出最好的作品,也找不出最差的作品,几乎看了令人想吐。为什么想吐?
朱 :这不仅是中国的艺术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从外部原因看,人类处在对社会未来缺乏乌托邦想象的时期,因此没有一个可供探讨精神议题的参照系。从专业本身来说,艺术的基本问题都已解决,比如各种媒介手段都已普及化,艺术与艺术史、政治、社会、文化等一切关系都涉及,艺术的进一步突破很难再仰赖社会转型、语言技术以及生活方式的非知识因素,而是要求一个艺术家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训练,大多数艺术家做不到这一点。
刘 :有人说,新世纪的十几年是中国当代文化和精神堕落的十几年,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朱 :可以这么说。
刘 :如果我们将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定在1990年代以后,那么你觉得它与现代艺术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
朱 :当代艺术的背景应该是消费社会、全球化和去西方中心主义,这一点确认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在90年代以后没有问题。西方的"当代艺术"发生于60年代末,一般将其看作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现代艺术"与"现代主义"是有区别的,中国实际上没有发生过西方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艺术。现代主义主要指未来主义、立体主义、抽象艺术等形式主义艺术。当然,中国是有现代艺术的,这种现代艺术我认为主要指政治现代主义的艺术,比如左翼木刻、政治宣传画等。在"文革"后,现代艺术应指一种反体制、反宣传艺术以及政治反讽的新艺术,这是发生在1980年代。

刘 :在中国,什么是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动力?
朱 :仍然是人性深处追求独立和创造的力量吧。
刘 :你觉得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是一种失控的状态吗?
朱 :主要是一种失去方向感的状态,不完全是"失控"。
刘 :当代艺术在中国与西方的形态不一样,那么中国当代艺术强调的应该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价值观又是什么?
朱 :作为一个有限开放的社会,中国与西方当代艺术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当然,中国在政治上仍未走出现代性,因此有关极权主义批判以及近现代史的精神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表达的领域,这是中国当代艺术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地带,但在过去十年被忽视了。另外,不应该过分强调中国当代艺术的身份特征,所有的艺术只能针对普适问题,即使中国特殊的部分,比如极权主义,它在中国是一个特殊存在,极权主义是一个普适的议题。
刘 :当代艺术最近几年遭遇到很多指责和咒骂,除了市场之外,与艺术家创作上远离现实、丧失社会批判性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很多艺术家逃避真实,与眼下的社会变革需要做出的自我牺牲精神相去甚远。对此你怎么看?
朱 :当代艺术处在一个专制主义仍未退出、全球资本主义的商业化初级阶段同时到来的语境。在某种意义上,当代艺术需要两面作战,既要批判专制主义,又要抵御资本主义。正如你说的,艺术人需要比以往更大的牺牲精神,才能有更深刻的艺术创作。遗憾的是,艺术界多数人对此缺乏深刻的认识。
刘 :我一直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者在任何一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都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 :是的。这个时代具备了创造伟大艺术的可能性,但艺术圈的知识分子精神提前耗散了。同时,新一代的艺术人在美术学院接受的是技术主义教育,缺乏看透现实所必须具备的人文训练。

刘 :21世纪以来,当代艺术的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艺术家在创作上缺少活力,缺少精彩的表达。你是怎么看的?
朱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这块土地,正邪双方正在争夺这块土地,因为双方都知道这块土地必将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未来。但中国的艺术界整体上缺乏世界的、宗教的、政治的宏观情怀和认识视野,当然,这跟中国的美术学院体系在知识训练上的"设计学院化"有关。
刘 :从当代艺术的层面上说,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缺少直面现实的态度和勇气,更缺少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敏感捕捉与把握的能力,90年代初那种敢于批判的精神和勇气哪里去了?
朱 :直接原因是被资本主义消解了,记得苏珊•桑塔格说过,资本主义对人的改造比极权主义更彻底。当然,中国的语境比这更严酷,因为资本主义背后还有极权主义这只手,这两只手在过去二十年将文化的批判性消解得比较彻底。
刘 :作家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晚宴上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文学和科学相比,的确没什么用处,但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你的看法如何?
朱 :艺术的"没用"是指他没有推翻现实权力的能力,"有用"是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颠覆权力的思想和美学基础。
中国几千年的文人传统一直有一个思想误区 :艺术和哲学可以绕开对现实权力的正面批判,通过自然达到自在的诗学境界。儒道释三派都认为存在一个比现实抗争更高的境界"自在",因此,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发现了一个人生升华的秘密通道,即不进行现实抗争,通过山水花鸟书法艺术可直接达到生命和艺术合一的至高境界。我觉得这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安慰剂,它涉及自由与自在的关系。自由即是抗争,你抗争了,你就处在一个自由的状态 ;你放弃了抗争,就表示你服从现实秩序,你又不自由了。儒释道强调通过修行达到自然、自在的境界,这是一个悖论,通过修行达到的"自在",实际上已经不自在了。
自在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不存在绕过自由直接通向自在的通道。在极权主义仍未退出的时期,不应过分强调一切艺术都不应该直面抗争,而追求更高的自在和无用,一部分批判的艺术仍然是需要的。
刘: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那一批当代艺术家以独特的语言表达了自省和自律,以及精神状态的改变和坚持,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展现并讨论人性的状态。然而在今天,我们无论如何是看不到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的,这究竟是为什么?
朱 :今天的时代,精神的困境及其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原因是抽象的,不再是像90年代初反应在生活环境、身体及其情绪等表层的直接体验上。每个人所直接面对的物质环境不再让人产生强烈的痛苦,人所受到的奴役和不平等体现在资本、政治和流行意识的结构性的总体控制,只有认识到这种总体性,艺术人才会有一种自省和自律,但这是建立在知识分子的知识训练上的。
中国目前缺乏有关这类文化总体性的公共讨论,这类公共讨论在80年代曾经有过,现在微博上有一些,但不成气候。
刘 :人人都是艺术家,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艺术的权利放回到日常生活中去,使其真正成为人的心灵拯救的途径。但是,我们今天的艺术体制又是在选择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所以这就与所谓的"人人都是艺术家"形成一个悖论。其实,这个悖论对艺术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想说的是,一个艺术家到底看重的是名利,还是灵魂的自我拯救?
朱 : "人人都是艺术家",是指人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常识经验基础上,像艺术家那样自由地思考和表达,不必追求像知识分子一样必须具备系统的知识训练后以专业的方式表达出来。但这不能理解为艺术从此可以随便乱搞了。
二战后,艺术成为一种学院派的游戏了,越来越强调知识的专家化和学院派的语言形式。艺术主要是反映一个时代影响人的灵魂、意识和人性后产生的问题,艺术需要找到一种恰当的语言形式呈现这些问题及其美学上的感受。
在极权主义时期,艺术品没有市场,反叛行为也被一律排除出体制,很难靠此生存。在资本主义时代,艺术可以直接成为生产性的商业行为,或者在反叛一段时间后,将反叛的符号当作一个品牌反复出售,此后,不再直面人的精神问题。中国的前卫艺术在90年代后被消解,这并非一个中国问题,前卫艺术与资本主义的戏剧性的转换关系,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发生过。

来源:N视觉

注:本站部分文章及视频来源于网络,如侵犯到您的权利请联系我们,我们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