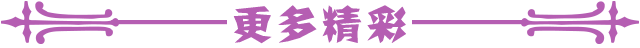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20余年中,张大力的艺术创作基本上围绕着若干重量级的实验性计划展开,其中的《对话》(1995-2006)、《一百个中国人》和《种族》(2000-2010)、《第二历史》(2005-2010)都属于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代表性作品之列。1这些计划中的每一个都引进了新的视觉材料和呈现方式。每一个都具有鲜明个性但又在深层概念上相互关联。每一个都包含了三个层次上的实验,一是对非常规媒材和视觉技术的发掘,二是与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社会的互动,三是对艺术家本人身份的反思。这些计划的复杂性与深刻程度使之具有各自的时间性:每一计划都持续了几年甚至十余年之久,但其历史维度不只是反映在时间的长度上,更主要的是体现为艺术家探索的不断深化。

图2.1“恒久与无常:张大力新作展”展览现场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一展厅
作为一个当代艺术策展人与研究者,我与张大力的合作与互动一直是这些实验艺术计划的组成部分;而我对他的注意也主要是以特定计划为核心,追溯每个项目的萌生和发展,发掘它所隐含的诉求和指涉。2在我看来,本次展览中的两套作品——汉白玉民工圆雕和蓝晒平面风景——也必须通过这种个案性的历史分析才能够理解(图2.1,2.2)。其原因在于二者都有着各自的来龙去脉,只有把它们放入张大力艺术创作的持续语境之中,我们才能发现每套作品中的实验性,发掘出它们的产生逻辑和历史意义。


图2.2“恒久与无常:张大力新作展”展览现场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一展厅
民工形象于2000年首次在张大力作品中出现,但是他对“民工”这个社会现象的考虑要早很多。他在2003年写道:“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有一种感觉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我想抓住它,并且想从最近的距离观察和了解其中的圭臬,它是一种氤氲的精神,和这种精神相吻合交融的就是我的同类……”3“同类”是理解他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一系列作品的关键词,但这个词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在写于2003年的这篇手记中它开始具有一种宏大和概况的意义,指的是“生活在亚洲东部、东距黄海的一个庞大的种族”。4但张大力在2000年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更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社会主体的能指(signifier)。这个主体就是在中国大城市中打工的各种外地人口,其中也包括“流浪北京”的他自己。5

图2.4张大力肉皮冻农民工手稿


图2.3张大力肉皮冻民工肉皮冻2000年
这一年2月,北京三里屯的时尚酒吧ClubVogue里举行了一场名为“艺术大餐”的当代艺术展示活动。6八个参展的艺术家中,张大力在酒吧墙上装上了一排不锈钢托盘,每个盘子托着一个用“肉皮冻”制作的棕褐色人头。人头的胶冻里混杂着犹如蛆虫的方便面,给观者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图2.3)。肉皮冻是北京老百姓的一种传统食品,据说是满族人发明、留传下来的。做的方法是把猪皮刮毛洗净,切成小块后加水煎熬直到猪皮与水合成一体。把胶质的液体盛入容器,凝固后就可食用。在张大力为这个展览写的方案里,他明确地规定了这个作品的四个施行步骤(图2.4):“(1)用石膏将十个民工的头翻下来;(2)然后去市场买足够的食用肉冻;(3)用锅(将肉冻融化)灌入翻好的石膏(模子)内;(4)放在已固定好的不透(应为“锈”)钢盘中。”很明显,这个作品的两个最关键的内在因素一是作为雕塑原型的民工,一是作为雕塑质料的肉皮冻。

在与《南方周末》记者朱又可的一次谈话中,张大力明确地说明了这两个因素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想,环境是一方面,这个环境(里)的人应当是更重要的,因为所有都是由环境里的人决定的,而且这些流动人口,从农村来城里打工的人,我认为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里最重要的人。他们的数目非常庞大,他们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会改变这个国家,表现这些人就是表现中国的现实。我想找一种材料来表现,你用铜或大理石去表现它都不合适,如果你的材料选的不对的话,跟你原来想的东西完全走到了反面。所以我好长时间在想怎么能找到一种材料符合他们,是他们自己。有一天我就在市场上溜达,我看很多民工他们来买肉皮冻,用小三轮车买一大堆,往建筑工地上运。肉皮冻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用肉皮熬出来的,它既不是肉,但又有肉的味道,有肉的一些油脂的东西,它又比菜贵,他们把它当肉吃,补充一些蛋白质。我想我能不能用这种东西去表现他们,他们的身份或者说他们的身体也是这样的,他们既不是人,又是人,没有人把他当人,但他确实是人,他是活着的,那这两个材料正好对应上了。”7

图2.5张大力思想牌绞肉机行为表演东八四条北京2000年
这个题为《民工》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多注意-——甚至当《巴塞尔文献展》(KasselDocumenta)的策展团队于当年访问北京的时候,张大力专门为他们在位于东四八条的“艺术家仓库”举行了一场称为“思想牌绞肉机”的行为表演,在场的奥奎?恩维佐(OkwuiEnwezor)等大牌国际策展人也未表示可否。可能他们并不理解肉皮冻的含义,因此也不可能懂得艺术家为什么用这种材料制作民工头像,又为什么把它们绞成碎末请在场者共食(图2.5)。但在我看来,这组以民工为题的早期作品——包括ClubVogue中的装置和东四八条的表演——在张大力的艺术发展中具有相当关键的意义。这个判断基于几个原因,首先是它们反映了张大力艺术探索的关注点从“环境”到“人”的转移。正如他在上面所引谈话的一开头所隐含的,他在90年代的主要作品《对话》所关注的主要是环境问题,通过现场涂鸦构成自身与巨变中城市的互动。但此时他认识到“环境(里)的人应当是更重要的”。第二,《对话》中的涂鸦头像所根据的是张大力自己的形象,8而在这组新作品中,他所考虑的“人”开始转变为现实社会中的他者。但这些作为“他者”的人与他自身又有着经验上的共同之处,因此构成了一种扩大的主体性。第三,这组作品在张大力的创作中引进了一个“物质转向”:“物质性”和“媒材”在他的思考中开始承担越来越重要的功能,与“形象”一起成为意义的多重载体。无独有偶,这也是他使用非常规的物质和技术制作雕塑和装置的开始。


图2.6张大力一百个中国人8月联展展览现场四合苑画廊北京2001年
这里我需要提出和说明一个比较复杂、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众所周知,“文革”之后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动向是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重新带回到艺术观察和表现之中,描绘和呈现城市中出售体力的“打工仔”的当代艺术项目在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也变得相当普遍。评论者对这个现象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持否定意见的人认为这类艺术品“只是将民工当作艺术材料”,“以低层形象和民众谋取艺术暴利”。9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艺术和社会现象,不可一概而论地进行价值评断。以张大力的肉皮冻《民工》而论,它们从来没有过商业价值,当时的张大力和其他许多实验艺术家也还未成名,谈不上“谋取暴利”的动机。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评论当代艺术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状况和艺术家创作的初衷。检视有关材料,可以看到张大力对民工题材之所以发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题材与他个人身份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与朱又可的同一谈话中,他拒绝把民工和自己“分成他们我们”。随即情绪激动地说:“知道吗?我的身份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别人,因为我是从一个小城市来的……毕业了我没有服从分配,就意味着我没有户口了,没有证件,什么都没有了。我后来的生活比民工更糟糕,是一样的,他们也一样。他们想摆脱土地,想来城市过更好的日子,但是没有关系,没有资本,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没有技能,所以他的生活道路更艰难,那么这些是谁造成的呢?是他自己造成的吗?这个由谁对他负责任?”10


图2.7张大力红色记忆展览现场798大窑炉2003年
张大力在这里所表达的是他与民工之间的一种本质上的认同而非具体的对等。虽然他在2000年已经脱离了圆明园画家村上顿不知下顿的生活,但是在他的内心里,在他深藏的情感中他仍然认为自己是民工的一员,是“他们”的同类。把民工头像转换为肉皮冻所传达的信息因此不仅是对于外部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质疑,也包含着基于个人生活经验的自讽和自虐。这两种含义在他在艺术家仓库实施的“绞肉”行为表演中被极端化:这个行为项目中被“消费”的不仅是肉皮冻这种材料,而更大程度上是那些面目不清的人头。

图2.8张大力一百个中国人玻璃钢26×22×20cm2005年
艺术家(张大力)与其题材(民工)的这种深层联系解释了这个题材在其艺术创作中的持久性。检阅一下张大力在此之后的作品,可以看到从2000年以来,他在至少七个重要项目中使用了从民工身上翻制的形象。这些项目中包括前面提到过的《民工》(2000)、《一百个中国人》(2000)和《种族》(2003),也包括了更近一些的《布朗运动》(2011)、《人与兽》(2007)、《广场》(2014)和本次展览中的汉白玉雕塑(2016)。在这个过程中,“民工”拷贝的意义发生了持续变化,从对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确切指涉转移为对种族和人类、暂时和永恒、现实与历史记忆等广义概念进行思考的手段和符号。这些形象的性质不再局限于对某种客体对象的“再现”(representation),而是被赋予了一种类似于“媒介”(medium)的意义,承载着不断变化的信息,提供了艺术家与观者进行交流的渠道。这些形象因此可以被认为是张大力艺术创作中的一种个人化的视觉语汇(individualizedvisualvocabulary)。通过对它们的组合、挪用、扩张和置换,也通过对它们的材料、制作技术与展示条件的控制和调整,张大力得以在他的艺术旅途中构造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的一条线索。


图2.9张大力一百个中国人翻制现场东湖渠北京2000年
创作于2000年代初期的《一百个中国人》和《种族》持续了由《民工》开始的实验,但是艺术家对于“材料性”(materiality)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图6,7)。在2000年的《民工》中,材料性直接显示为作品所使用的肉皮冻物质。虽然塑像的制作需要用石膏首先在民工头上翻制模型,但这个程序在作品的概念中并没有被强调,在展示中也没有突出呈现。张大力很快意识到这个“翻制程序”的重要性:一旦抛弃了绘画和雕塑的工具而采取直接模制对象的手段,所拷贝的民工形象自然模糊了“再现”(representation)与“表现”(presentation)之间的界限,因而也颠覆了常规意义上的艺术表现规则。而且,这种直接拷贝所记录的是对象在特定时刻的特殊状态,因此必然具有刹那或瞬间的性质。张大力对这种“瞬时拷贝”(instantaneouscopy)的自我意识反映在他突出了对《一百个中国人》和《种族》翻制过程的表现,使这两件作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从最终的制品转移到“瞬时拷贝”的过程。“材料性”的定义因此也不再局限于雕塑所使用的物质,而更主要的是指人与材料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在制作过程中的互动和转化。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肉皮冻《民工》以其具体的物质存在呈现了一个静态的社会寓言,《一百个中国人》和《种族》则是通过对翻制和互动的记录和呈现,在“当代艺术”的名义下对于商业社会中的权利关系和经济运作进行了缩浓和反思。


图2.10张大力种族工作现场北京2005年
我们需要意识到这样做对艺术家本人是有风险的:不但他与民工模特之间所缔结的暂时雇佣关系复制了他所计划反思和批判的社会权利关系和经济运作,而且他所设计的从对象身上直接翻制石膏模型的方法,也“拷贝”了这种权利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实用性和残酷性。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张大力的处理方法是暴露拷贝人体的过程和操作。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经常指出权利运作的一个常规是尽力隐藏自身的存在,但张大力不但在石膏头像和人体上有意地保留了直接翻制的痕迹(图2.8),而且使用摄影记录的方式把《一百个中国人》和《种族》的过程转化为艺术表现对象,因此把一个可能出现的艺术伦理的问题转化为前卫艺术的自我边缘化(图2.9,2.10)。在《一百个中国人》的展览图录中,八幅现场照片记录了受雇民工在鼻孔中插着塑料管,头和脸上被厚厚的白色石膏覆盖——我们可以想象这种状况下他们的所承受的不适(见图2.9)。11

另一些照片则记录了模特的邻居或亲人在民工住宿地里观看计划的实施,他们脸上的表情从好奇到无动于衷(图2.11)。还有一些照片则是模特本人与自己石膏像以及与艺术家的合影(见图2.10)。当这些现场拍摄的记录与翻制的三维头像或全身像放在一起展示,它们共同构成的是一种移动和转化中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其游离闪烁一方面模糊了原型和作品的界限,一方面也拒绝模特与图像的二元性凝固对立。面对着这些照片和塑像,人们可以认为被雇佣的民工模特被异化为无生命的物体,但也可以想象这些从身体上直接翻制下了的形象仍保留着皮肤的接触、温度甚至情感。在这后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张大力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些作品含有“灵魂”,为什么这种直接的瞬时拷贝是他可能找到的对人类存在最敏感和真实的记录:“当我用这种最原始的拷贝方法记录下这个种族的每一个个体时,我相信也会瞬间凝固潜藏于他们肉身之内游走的灵魂。每一个不同外貌的躯体就是他们灵魂岩浆在内涌动所形成的地壳,有什么样的灵魂就会创造什么样的肉体,这个拷贝的肉体是他们灵魂的标本。”12


图2.11张大力一百个中国人翻制现场东湖渠北京2000年
1、有关这些艺术计划的全面报道,见《张大力》。武汉:合美术馆,2015年。
2、我与张大力的首次合作是2000年的“艺术大餐”展(与张朝辉共同策划),并对张大力做了访谈。我对他的“对话”系列的评论首先出现在PublicCulture12.3(2000),749-68.文章的题目为“ZhangDali'sDialogue:ConversationwithaCity。”随后在我主策划的“首届广东三年展”(2002年)和在纽约和芝加哥举行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中国新摄影和录像”展(2006年)中展出了这组作品。张大力的《第二历史》首次与2005年10月在798艺术区展出,我担任该展的策展人。其后在“第六届光州双年展”、芝加哥Walsh画廊、柏林世界文化宫等地展出这件作品并发表讨论文章。本次展览和图录可以说是第四次主要的合作。
3、张大力:《种族》,2004年12月。载于《张大力》。武汉:合美术馆,2016年。365页。
4、同上。
5《流浪北京》是纪实电影人吴文光在1988到1990年间拍摄制作的一部片子的名称,张大力是其中所记录的4名流浪艺术家和文学家之一。
6、此展览由张朝辉与本人策划,具体情况见巫鸿:《关于展览的展览:90年代的实验艺术展示》。北京: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2016年。230-237页。
7《朱又可采访张大力》,《南方周末》2009年4月2日。载于《张大力》。武汉:合美术馆,2016年。337页。
8、在一次访谈中他解释了他的涂鸦人头像:“这个符号来自我本人的形象,是我本人形象的抽取,我用这个符号代表我和这个城市进行交流,我想了解这个城市的情况,它的变化,它的结构。我把我的这个行为起名叫‘对话’”。见冷林《和城市“对话”—张大力访谈》,冷林《是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第168页。
9、朱其《当代艺术中的底层社会:政治隐身个体缺位》,华夏收藏网http://new.cang.com2015/12/3。
10、《朱又可采访张大力》,《南方周末》2009年4月2日。载于《张大力》。武汉:合美术馆,2016年。337页。
11、《张大力:一百个中国人2001-2002》。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2002年。5-18页。
12、张大力:《种族》,2004年12月。载于《张大力》。武汉:合美术馆,2016年。365页。
来源:艺中

注:本站部分文章及视频来源于网络,如侵犯到您的权利请联系我们,我们将立即删除。